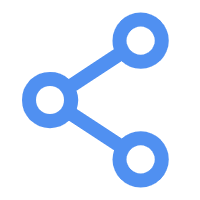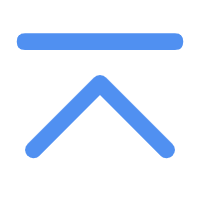中观精要善说·龙树心庄严
讲述:根敦群培
整理:达瓦桑波
(首礼赞:赞佛)
魔罗射来利箭,您以鲜花回赠,
提婆达多嗔心攻击,您持戒不语,
面对怨敌,您眼中没有丝毫恨意,
您是摧伏恐怖轮回大敌的善导师,
一切智者无不向您敬顶礼。
(赞师 :弟子达瓦桑波,即记录和整理此讲记的人,赞颂其上师根敦群培。根敦群培汉语意译为善求法增。此偈使用藏文诗学里的藏头诗,将根敦群培:根为善,敦为希求,群为法,培为增上,四字嵌入此偈每句的句首,以作礼赞。)
善妙清净甘露之源解脱道,
求索,开演中观之法眼,
法王尊胜语狮子,
增减俱无,故诸理士向您恒顶礼。
(立誓:达瓦桑波):
生习二慧虽卑劣,
慧日坛城普贤之法界,
依然于我莲花苑般的心田中显现;
闪耀着万千光芒的正理善说,
如盛开的馨香花蕊;
愿三界智者,
如花间采蜜的蜜蜂一般,
尽情享用“自性光明”之甘甜。
(《中观精要·讲记》音频25条/5分24秒。慈师说他有《中观精要》的传承,是从堪布阿智那里接来的;堪布阿智是从藏族当代四大学者之一的年叙·钦热唯色(宁玛派)那里接来的;年叙·钦热唯色是从本讲记的记录整理者达瓦桑波那里接来的。他俩当时是同事,在位于拉萨的西藏大学任教。)
根本而言,我们对一切有无是非的判断,都是基于它们在我们能所二取的心里如何显现而确定的,除此而外,就没其他什么依据了。人们通常会问:“有吗?”对方会答复:“有。”但这个问答实际上应该是这样的:
问:“你心里显现的是个有还是个无?”
答:“我心里显现的是个有。”
我们关于好坏、善恶、美丑的一切问题,都是为了弄清楚对方心里的显现的是什么而提出来的。对方的回应,也仅仅是根据他心里那时那地、那情那景的显现作出的回应。因此,两个人之间的争论无非就是二者的显现不一而导致的。两个人相互认同时,会将所谓的可被共同认知的事物纳入是、存在、所知和正量的范畴。基于这个原因,可以说对某个问题认同的人越多,那个问题就会成为备受推崇的主流观点,而与它相异的观点,则会被贴上邪见和错误认知的标签。
人类的认同方式千差万别:有人会依据经典而达成共识,比如两位穆斯林教徒之间关于是否能吃骆驼肉的争论,最终会因为《古兰经》里说了可以吃骆驼肉而盖棺定论,达成共识。有人会依据逻辑推理而达成共识,比如山那边是否有火的这个问题,会因为眼睛现量看见了山顶升起的烟,双方因此达成有火的共识。这种通过根识现量所见而平息争论达成共识的情况适用于所有凡夫。
那么是否可以拿着“所有人都认同”这一点作为依据,去判定所认同的这个问题是不欺的真理呢?答案是否定的。比如,某个地方,因为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患有胆病,因此他们会一致地将白海螺看成黄海螺。事实上,仅凭这一点,是无法证明白海螺是黄色的。就算所有人类,乃至三界所有众生,都一致认定白海螺是黄色的,那也无法承当成立白海螺就是黄海螺的真因。如此说来,我们对一切有无是非的判定都只不过是基于自己心前的显现方式而已。当很多有着相似显现方式的凡夫聚集到一起时,他们所认同的所谓的“真理”就会成为不容触碰的金科玉律,而与之不同的声音则会被说成是异见邪说,备受抨击和贬斥。
我们所说的有,实际上属于凡夫心能显的那部分法;所说的没有和不可能有则属于凡夫心无法显现的那部分法——非有非无的法性是属于后者的范畴。
像多数派靠着众口烁金的本事将少数派贬斥为骗子的例子,月称论师在其《四百论广释》中对“是故世间众,何谓不癫狂”这个偈子进行解释时,曾用一则故事来讲:以前,某国的一位占卜师去见了国王,他告诉国王,七天后这里会下场雨,凡是喝了雨水的都会变成疯子。听后,国王叫人把自己喝水的井口封上,不让雨水落入井中。但是他的臣民们,因为没能这样做,喝了雨水,成了疯子。这样一来,举国上下,只有国王一人是正常的,他的言行举止自然和臣民大相径庭,格格不入,因此被臣民说成是疯子。最后,国王实在是没办法独善其身,只能无奈地喝下那雨水,成了疯子,与臣民一道“同流合污”。
所以,从无始以来,被无明水灌成了超级大疯癫的我们,对有无是非问题的认定其实是错乱不堪的,根本不可靠。一群疯子的疯言疯语,即便他们之间再怎么相互认同,却压根无法成为判定这些问题的真实依据。
作为佛陀追随者的我们,对我们所认定的这些有无是非等问题,因为佛陀早已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因此不需要任何其他真实依据去证明真伪,可以想当然地认定它们绝对是无欺的。如此一来,就必然牵扯到另一个无法规避的问题:谁来证明佛陀是无欺的呢?如果说是龙树菩萨等印度大智者大成就者们,那么请问谁来证明龙树菩萨他们是无欺的?如果说是至尊宗喀巴大师,那么请问又是谁知道宗大师无欺呢?如果这时你又说你的某位无与伦比的大恩上师,如此一来,最终那个判定者就成了你自己。这种做法,无异于老虎证明狮子,牦牛证明老虎,狗证明牦牛,老鼠证明狗,虫子证明老鼠,兜了一大圈,到头来虫子却成了大家最后的判官。因此,所有问题,当我们深究时,无一例外地都是自我在自作主张。
那么,由能所二取的心所确定的种种事理,是否可以成为我们所能依靠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呢?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被自我蛊惑的心像一位九流卦师卜的卦,时而感觉对,时而感觉错,但究其根本,从未对过。如此迷乱的心,哪里值得信赖?明明早上确定的事儿,下午就变卦了;上半辈子信誓旦旦的事儿,到了下半辈子,连个影子都见不着;一群穆斯林认定的真实,却被一群佛教徒说成是假的。然而,这两帮信徒都有各自认为像金刚一般无所不破的经典和教理,也都毫不怀疑地认为自己的导师是真实的皈依处。好了,这个时候,又是谁来判定孰真孰假呢?
如果说仅以持相同观点人数的多寡不足以判定什么是真理,还需要以正量来进一步判定的话,那么这个正量又是什么样的呢?如果说眼睛现量所见的柱子是以正量成立,所以这个能见的心是正量,那么如何去证明这个能见的心是无欺的?在尚未证明柱子的有无之前,是根本无法知道这个能见的心是正量。反之,尚未证明能见的心是正量之前,也无从判定柱子的有无。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将一直无解。
当然,我们会说证明柱子有的原因是它能被眼睛看见,被手触碰,还能被其他人看见。这无异于在重复前面的说法——眼和手达成了共识,在此基础上,还加上了第三方的共证,所以“柱子有”就该是真理。但这个说法不一定可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去说眼识,手的触识和他人的共识是绝对不会出错的。之前说过,两位胆病患者会同样地把白海螺看成黄海螺,也能同样地去触摸它,而且会一致地认定它是黄色的;但事实上,不是他俩都错了吗?
通过诸多教理的建立,我们试图去证明有无是非这些问题背后的判定者并非是自我,而是佛陀、龙树菩萨和祖师大德们;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些冠冕堂皇的论述背后,那个最终的判定者正是那个二元的心。真正的智者们都说二元的心是迷乱的;这样一来,我们用来判定一切的这个所谓的根本就错了——根烂了,哪里还生得出真理的果?
轮回里的判定者,除了这个迷乱的二元心外,不会再有其他了。而依靠它,对法性,出世间法和万法远离名言戏论的本体的思量和所作的名言安立岂不是大错而特错呢?
世俗的一切假法都是由它们的源头这个二元的心所确定的。可是,真心致力于寻求胜义谛的人们啊,要知道说谎的心,它尾巴长不了。这很重要。
总而言之,如果真能拿出一个究竟的颠扑不破的理来证明能所二取的心不是迷乱和欺惑的,那么可以同样去证明其他很多假法是不欺惑的。但是,这些所谓的理由全都是牵强附会,生搬硬套和自我陶醉。月称论师在《入中论自释》中指出“因为是真理,所以是真理”的说法是无法成立的。同样地,执持一个它不是迷乱的理去固执己见地说它本身不是迷乱的,是行不通的。谎话说了一千遍,它终究还是谎话。
凡夫的心是迷乱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即便是圣者,他们的论断也会被否定。比如一切有部佛音论师所持的外境实有的观点被无著菩萨遮破。而无著菩萨所持的遍计外境不实有,仅是依他起的观点被后来的中观师遮破。这些大智者们的论断尚不能完全取信,遑论凡夫的完全迷乱的心?
诗云:
看我的心,
婴儿到暮年,
刹那变化;
此时可觉知的念头,
不真实。
既然什么都不值得信赖,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就像之前所说的那样,在世俗,就只能姑且相信那些假法,依靠那些假法,以假说假,仅此而已。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相信现在所看到的山河大地,成佛时还能照样看到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慈师说这里是在反驳格鲁派提出的中观八大难题中的于佛果位时尽所有智的承许方式。)毛驴依靠它毛驴的分别识就能感受草的甘甜,而当那个分别识和它的躯体分离时,当毛驴不再是毛驴时,它那样的感受力也会随之丧失。公鸡报晓的明力会因为它的这个分别识和躯体的分离而消失。
如果我们人类在五根的基础上多些其他根的话,我们所能认知的外境将会更加的纷繁复杂。如果双眼的位置不是左右横排,而是上下竖排的话,我们所见色法的形状和颜色必定是大相径庭的。
我们的所有认知完全依赖五根,但我们五根的认知力极其有限,比如,我们的眼睛无法看见任何肉眼不可见的色法;我的双耳也不可能听到任何超出人耳能识别范畴的声音。但是,我们却断定孱弱的五根加上一个迷乱的心,能摄尽万法,并且说那个尚无法于自心显现的实相是没有的、是不可能有的;对这种见解的志得意满便是堕落之门。
佛陀早已清晰地宣说过了人类五根无法认知的领域。《三摩地王经》中说:
眼耳鼻非量,
舌身意亦非。
若诸根为量,
圣道复益谁?
修行圣道的究竟要义,是为了找到思维中从未出现过和肉眼从未见过的那个东西。但是,当认真观察我们所承认的那种出世间法时,会发现它仅仅是这个情器世间的复制品而已。比如,因为我们喜欢珍宝,所以密严刹土里的庭宇楼台都自然而然地由奇珍异宝构成,佛的圆满报身的庄严三十二相,实际上都是符合我们人类审美的形色和装饰而已。
在印度,佛的报身和本尊的装束,如果细究,都不难看出是在模仿古印度国王的扮相。这些不是人类意识编造的,因为这在佛经中也有记载。当然,这也仅仅是让我们能够清晰和充满意乐地观想佛地功德的方便而已;到了汉地,佛陀在密严刹土显现的报身必定是长髯加龙袍;到了藏地,密严刹土里,佛陀面前会供养一个五百由旬大的金色茶桶,里面盛放着如意牛的牛奶制成的新鲜酥油,边上衬以如意树的枝叶。
这些都是我们凡夫意识的分别念而已。佛陀的行处,正如月称论师所言:“您的密意却是无法言说。”尽管说给我们听了,但无异于“对牛弹琴”。
如果对佛陀的不可思议的密意有些许的信心,那么对佛陀所宣说的长劫和刹那无二、微尘和宇宙无别也应当生起相应的信心。
我们的能所二取的心若是正量的话,就等于承认无方微尘是色法的最小组成单位,宇宙是没有边际的,以及“小”不可能装下“大”,因此,不论佛陀如何神通广大,也不可能遍知正量所建立的这些理。如果假设可以的话,那么请问佛陀能使万法实有吗?能让众生成佛吗?答案是“不能”的话,不能的原因只能是万法不实有,众生不是佛,否则为何说不能呢?
如果我们说微尘和宇宙大小无别妨害了世俗谛,成了断见,那佛陀现量证成大小无别的过失岂不是很大?先断定微尘和宇宙大小有别,然后再去说佛陀是随顺各种特殊因缘而示现大小无别,这种说法就足以证明我们自诩的正量其实千疮百孔,无法自洽。
真明白的话,就该知道,佛陀示现微尘和宇宙大小无别,不是为了证明他拥有何其强大的能力,足以化有别为无别,而是在向我们昭示:我们能分别大小的有限的二元认知,根本无法了知佛陀本具的无限的无二慧。佛陀那里,无大无小,一味平等。大小本无别,佛陀只是如是说而已,并非是在无中生有。
因为我们的有无、是非、大小和好坏等所有二元认知,都是相违的分别念,所以才会出现微尘容不下宇宙的说法;但这其实是我们的分别念,假借名言安立,上演的一个“超级神通秀”。要明白,让这个“神通”现前的正是我们自己,而并非是佛陀。
《入中论》的序言中记载了月称论师以画牛挤奶的神变摧伏他人执著实有的事迹。如果画牛实有的话,那它不可能有心肝肠肚乳头之类的内外器官。如此说来,画牛可以挤出牛奶,是月称论师对缘起的“诋毁”,而非遮止了实有。
噶当派的经典中记载,当阿底峡尊者显现进入只有巴掌大的擦擦模具杯中和其他神变之后,对身边的人说到:“我们今天在此所见证的一切,是那些逻辑推理学者们无法理解和接受的。尽管如此,我阿底峡敢当着印藏两地所有智者的面起誓——这正是法的实相。”
我们习惯性地执著于“非无即有、非有即无、非大即小、非小即大”的二元观念,认为这二者是直接相违的对立面,有无之外,不会再有其他可能性。如果有无、大小之间没有差异的话,我们会惊呼所有的缘起法将会因此崩散殆尽。认为法性远离四边八戏的这个见解是极大的断见,恰恰说明我们的二元认知,除了能分别有无的二元法外,是无法去了知远离有无的法性。因为我们能所二取的心无法现前法性,所以说它“不可能有”和“没有”,纯属无稽之谈。
对过去的藏北牧民而言,因为牛奶是他们食物中唯一带甜味的东西,因此凡是甜的必定是牛奶的认知,在他们的心里根深蒂固。一个不是牛奶和又是甜的东西,对他们而言,绝对是超乎他们想象的相违法。这种见解是也会被视为诋毁世俗谛的邪见。
再举一个例子:张三和李四是王五唯一认识的两个人。如果说王五知道一个屋子里只有一个人,而这个人又不是张三,那对王五而言,此人必定是李四,因为王五就只认识他俩,所以不是张三就该是李四。
我们的心,除了在有无上面不断交替分别外,根本无法安住在远离有无分别戏论的法性里。
佛陀说中观是离开有无二边的中道,比如,《佛说大迦叶问大宝积正法经》中云:“迦叶,有是一边,无是一边,二者之中道,即是中观,不可言思。”《大宝积正法经》中云:“有无是诤,净垢是诤,是诤苦不息,无诤则苦灭。”
但是,如今的学者们一听到某个关于非二元的教理,首先关心的是这个教理的出处。如果它是藏地前译派的某位智者说的,他们便会说他是持断见的愚夫;如果知道是佛陀或龙树菩萨宣说的,则会说此处的非有是不实有的意思,非无则是世俗中非无的意思。为自圆其说,他们会添油加醋地说一大堆东西。事实上,他们这样做,一是害怕背负谤佛谤法的罪名,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二是通过批判前译智者们,获得智者和勇士的美名,受人尊敬和拥护。
虽然,有无、是非、离开言说、离戏等词汇出现在佛陀所宣说的经中的次数,和出现在印度智者所造的论中的次数,以及出现在藏地前译智者们的论释中的次数不相上下,但是对后者所说的“不可思议”的见解,有人直接给它贴上愚者的断见进行批驳;有人会稍显恭敬地说藏地前译智者们所诠的宗旨并无大碍,但是不及宗喀巴大师那般细密。如果这些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也可以说:佛陀的意趣固然是周遍一切的,但当借助语言去宣说时,却是“无可言思般若度”,而这显然对“确立有和非有都得依无患根识前显现的相而论”(引号里面的是格鲁派的说法。根大师对此进行批驳。)这类补丁式的阐述有弃置不顾的嫌疑,所以佛陀的说法也可以被视为缺乏严密性。
因此,希望对藏地前译和佛陀的破立能一碗水端平,不要因为怕遭口舌,而当了骑墙派,满嘴胡说八道,四处蛊惑人心。
(慈师说这一部分的说法和以龙钦巴尊者、全知麦彭仁波切和全知果让巴为主的前译派智者们的说法完全一致。)抉择胜义谛时,就得深深地相信我们能所二取的心所确立的一切,都是无中生有的臆造而已。这样思维时所产生极度的恐惧感,也正是对空性见产生的恐惧感。我们思维中的有无,是非,净垢,好坏,佛与众生,善趣与地狱等都想当然地被视为无欺的缘起法,不能遮破,一旦遮破,就成了断见。但是,找一个所谓的独立于这些现象之外的实有法去遮破,不过是一些善于耍嘴皮的学者玩弄的文字游戏而已。
按照他们的观点来说,通常我们相续中执五蕴为我的分别念并非我执,所以不用去遮破。那么,通过下面这个例子,来看他们如何安立俱生我执:某人说你是个小偷时,你心里生起的“我怎么会是小偷”的那一坨“我”的感觉被说成是俱生我执。
“执五蕴为我”的心若是正量的话,当“我”被说成是小偷时产生的这个执我的分别念,只能说是正量的分别力变大而已,怎么能说成是实执呢?如果硬要说它是实执,那么当人说“佛陀并非皈依处”时,你心里生起的“佛陀怎能不是皈依处”的念头,又有什么理由说不是实执呢?
如此一来,听到“瓶子非瓶”时,心里产生的“这绝对是瓶子”的念头是对瓶子实有的执著,而并非是正量。因此,依照他宗的这个承许,势力尚小的分别念应是正量,而当它势力变大,显现出来时,它就像人体内的风从维护健康的卫士变成致病的病毒一般,忽地从正量变成了实执,这种说法不得不让人“拍案叫绝”。
落实空性见,获得证悟,认识所破至关重要,这一点应该是所有人的共识。宗喀巴大师说过:“未证悟空性之前,根本无法去区分如幻有和实有,如幻无和实无之间的差异。”这也正是中观应成派和自续派之间没有所谓共同承许的有法的究竟原因。”那么,这也就是说,在没有证悟空性见之前,单独去认识一个自性实有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所谓的认识所破不可信。
有些人会这样说:“确定瓶子有的正量识产生时,瓶子自性有的分别识也会同时生起,很难区分这二者。”“正量是获得佛果的主因,实执是一切过患的根源”,但令人诧异的是,这两个貌似合理的说法,实则根本无法自圆其说。这二者,一个生起时,另一个也必定同时生起,那么遮破时,也必须同时遮破,而不能将它们割离开来。
“天亮了”这个分别识是正量,“系腰带”这个分别识也是正量,以此类推,接下来的吃饭喝茶等所有分别识都是正量,那么一整天所有的分别识里头就不会有一个需要遮破的法,这样一来,实执这个所破到底什么时候会生起呢?无始以来,对实有的执著就在我们心相续里不断地被串习,已经到了“不思量,自难忘”的境地,但按照刚才的说法,一天之内也,它可能偶尔出现一两次,不得不说“实执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事实上,我们心里出现的第一个分别念的始作俑者,往往都是心相续里最习以为常的那股势力;比如,某人的父亲是诺贝尔奖得主,当他看见父亲时,心里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我父亲来了,而不会是诺贝尔奖来了,或者诺贝尔奖得主来了。这个也正是佛法因明典籍里所阐述的观点。
无始以来,我们相续里最习以为常的那股势力是对实有的执念,因此,一见瓶子就会起的分别念,绝对是对瓶子实有的执念。理论上,我们可以换着各种花样分析这个所破,但真去破的时候,要破的就是这个瓶子。破柱子也罢,破有也罢,破无也罢,我们不能放着瓶子不去破,反而找一个所谓瓶子的实有去破。这一点,不仅是藏地前译智者们所持的见解,也是格鲁派里面教证齐全的智者们所秉持的观点。比如,格鲁派章嘉仁波切如是说:“放着眼前这明晃晃的显现不破,而去找个兔角来破,此举着实不可取。”格鲁派高僧贡唐丹贝卓美大师和第四世班禅大师洛桑曲吉坚赞都同样秉持这一观点。(慈师说格鲁派指出章嘉仁波切所说的“明晃晃的显现”指的是在显现上产生的实有感。对此慈师予以反驳:显现上产生的实有感就是这个明晃晃的显现,这个明晃晃的显现就是显现上产生的实有感,没有一个独立于这个显现的东西叫实有,所以要破的正是这个明晃晃的显现。比如破柱子,就是要破明晃晃显现的柱子,而不破在柱子上产生的实有感。慈师说麦彭仁波切也对章嘉仁波切的观点作过阐释,称其所持的观点与前译的中观见完全一致。
格鲁派对根大师的看法不一,其中格鲁派拉让巴格西哲霍·达瓦泽仁的看法中肯,所以将他的大意翻译后放在此处,仅供参考。这位格西在谈到《中观精要》时说:“根大师《中观精要》文采飞扬,对中观有其独到的见解。我们应该遵循往昔诸大德“于其人修清净,于其言善甄别”的教导,摒弃地域和教派偏见,怀着一颗求真的心去反复品读。这也正是佛陀的精神:“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语,如炼截磨金,信受非唯敬。”他说格鲁派里面那些说《中观精要》即非前译又非后译,完全是根大师自创的一个全新宗派的说法,说明他们根本没有好好研读过前译的中观论典。《中观精要》的意趣完全是前译派的中观见。但根据慈师的讲记,可以看出,根大师在《中观精要》里的有些观点和说法与前译还是存在差异的。但总体上,根大师的观点和宁玛的荣森班智达、龙钦巴尊者和全知麦彭仁波切的意趣是相同的。
达瓦泽仁格西指出,虽然根大师的《中观精要》值得深研和赞叹,但是其中的不当之处,也必须指出来。他说根大师对章嘉仁波切所说的“明晃晃的显现”的阐释是完全错误的。章嘉仁波切在他所造的《章嘉宗义》里面所说的“明晃晃的显现”根本不是“不破实有而去破显现”的意思。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中观精要》里说格鲁派高僧贡唐丹贝卓美大师的和第四世班禅大师洛桑曲吉坚赞都赞同章嘉国师的说法,但是阅遍四世班禅大师五大部文集和贡唐大师八大部文集,别说他们几位持这样的见解,甚至连稍微类似的说法也找不见只言片语。”慈师说班禅大师有没有这样说过这样的话,他本人还没有见到过,但他在贡唐大师的文集里面见过类似的说法。
有人担心,以理遮破显现的柱子和瓶子的话,会产生什么都没有的断见,这种担忧纯属杞人忧天,因为面对眼前显现的这个如此真切的瓶子,我们凡夫不可能认为它根本不存在。
如果真能这么认为的话,那我们看着眼前正显现时的这个瓶子时,尽管它看得见摸得着,我们自然就会明白其实什么都没有。所以,知道它现起的同时本无,这正是现空无二的中观见,何来断见一说?因为心里已经确信了瓶子本无,所以当眼睛现量看见瓶子时,便会直觉性地知道它是如幻的,因此不会有堕入断见的过患。
有诗云:
心中确信无,
眼里看时有,
黄帽虽未学,
幻心本无生。
将黄金、土石和草木一起置于火中焚烧,会被烧尽的自然会被烧尽,烧不尽的自然会留下来;同理,虽以胜义观察理遮破所有显现法,但后得位时如幻的显现一定会一直在那里。但是,首先把如幻的缘起独立开来,放在一边,尔后再说不要以理去妨害它,这纯属画蛇添足。(慈师说根大师这里的说法和麦彭仁波切在《中观难点阐释宝箧》中的说法一致:不要把瓶子和瓶子上的实有区分开来,二者都要破。)
虽然不承认名言谛,但又不会怀疑缘起,为什么会这样呢?所谓名言正量,美其名曰,是为了对世俗中粗大的现象进行细致的“格物”,学者们利用三相推理等理证方法建立起来的一门世俗认知系统;但实际上,因为学者们需要在众生遍计无明现前的外境上安立名言的差别法的缘故,他们便通过逻辑推理法去凸显这些差别法。因此,可以说无论以所谓的正量、可信、无欺、无误等词藻去修饰名言量,其本质不过是学者们通过逻辑推理造作的名言差别而已;无论学者们所造作的差别法如何纷繁复杂,但究其本质,这些不过是在说六道众生相续中的分别识,依据各自的业力朝向,显现上出现的差异而已。
比如,儿子的手遇到火,就会疼得嗷嗷叫。他这个是无欺无误的现量。父亲责骂儿子说血肉之手遇上能烧之火,自然会被其灼伤。父亲这个讲道理的做法就像佛教以教理量成的做法。因此,只要山河大地的显现没有消失,那么三宝、因果、缘起等显现也不会无故消失。根据自我需求决定显现是否需要消失,凡夫顽劣的本质由此昭然若揭。
有一天,当到了过去的老密咒师们所说的法性遍尽相的境地时,山河大地、缘起和三宝等这些好、坏和无记的世俗法会从根本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超越二元的,诸如身意相融(色身和法身相融)、二谛相融、好坏相融、善恶相融等不可言思的境界。这时,无量分的尽所有智,最终将归入如所有智的那个本体。
总的来说,凡夫的这个“信”可谓五花八门:真心的信、违心的信、模棱两可的信,不过归根结底,最终相信的还是自己的显现。这里所谓的信,是指心不由自主地,跟着感觉,堕入片面化的认知樊篱。
梦中显现的种种,尽管没有人会认为是真实的,但梦中出现的苦乐恐惧等感受,我们却会不由自主地认为是真实的。比如,以三相推理去分析梦中从陡峭的山顶跌落的结果,结论是必死无疑,但梦中出现的下坠后再次腾空飞翔等这些现象是逻辑推理所无法成立和解释的,但毋庸置疑的是,伴随这些显现,心里还会无欺无误地产生下坠时的恐惧和腾空时的喜悦等相应的感受。这好比是鱼在水中的惬意和溺水之人在水中的恐惧,对他们而言是无欺无误的现量,由不得他们不信。
中观应成派自宗对自方和他方承许的差别有不共的诠释:尚未摆脱二元认知习气的凡夫毫无自主可言,因此对他们说的有作出的暂时性的认同,这是他方承许;而已经证悟法性的瑜伽师自方对凡夫的见闻觉知的任何一法都不予承许,正是应成中观所说的“我什么都没有承认过”。(慈师说这正是麦彭仁波切等前译上师们的意趣。月称论师说所谓世俗谛是依他而说。依他而说也要分二:一是在诠说真如时,不需要考虑世俗,因为毫无妨害;二是在与世俗对话时,要依世俗作出他方承许。自续应成二派的差别在于:如幻如梦是自续派自宗的如幻如梦,因为自续派自宗承许二谛。自续在抉择胜义时,遮破自性实有,留下了如幻如梦的显现。应成派说名言都是他方承许。虽然麦彭仁波切在其《定解宝灯论》中说应成有他方承许,但是那也只是自方仅依他而说的他方承许。)没有承许的立论者(应成派)安住在离言等持中,而有承许的驳论者(自续以下的宗派),会以教证和理证的方式与其进行辩论,只要前者开口回应,都将无一例外地变成承许,因此,“没有任何承许”的这个甚深见,是超越语言,特别是逻辑推理范畴之外的一种超认知。
总而言之,自方打心里承认大地是有的,这叫自方承许;自方不得已而暂时去认同他方认为大地有的这个观点,这叫他方承许。多陀阿伽陀(如来),在菩提树下,七昼夜不休不眠,证得妙觉,这是佛陀的“没有承许”。为了让众生证得实相,而转四圣谛之法轮,是佛陀大悲心使然的他方承许。这不仅仅是应成派的看法,其他任何秉持了不了义二谛见的宗派也是这么看待的。
《释量论》中云:“彼舍真实义,以象王顾视,唯顺世间心,趣向观外义。”佛陀博伽梵在说法时,也会因他方而暂时承许外境的有,这在印度智者所造诸论中可窥一斑。
从自他两种角度出发,每个人都具有两种思维方式、认同方式、阐述方式,因此,要求佛陀和众生所有的显现和说法都必须完全一致,这岂不是痴人说梦?
如今佛学院里那些平庸的辩论,何须畏惧,对方发出的任何“太过”,无需作出其他回应,仅“不承许”就足以在谈笑风生间将其遮止,化于无形。
基于凡夫分别念的三相推理,在某种层面而言,最好是看成自己收拾自己的方法,如果想把它当成劈砍“没有承许”这个见解的刀剑来使的话,对于证悟法性而言,就是自塞悟门了。对此,陈那论师在其《集量论》中作了明确的宣说。
偈颂(慈师说这些偈颂估计不是达瓦桑波听课时所作的笔记,而是根大师写的偈颂。):
有无别识安立之所知
观待真假外境之正量
此说彼假彼亦说此假
安立名言之量心不安
不经观察世间之学说
观察辨析宗派之教理
二者盘根错节相依存
安立名言之量心不安
于心显现诸相皆如幻
于义深深了知是空性
此若为真观彼则成假
安立名言之量心不安
欲遮如山己过立论者
索瑕他人过失驳论者
二者胜负犹如轮盘转
安立名言之量心不安
遮破有边“现而不得因”
断除无边“不现不得因”
二因所立各自为妨害
安立名言之量心不安
贪著朋友之相之实执
了知朋友利益之正量
皆是贪爱无处觅不同
安立名言之量心不安
执著怨敌为有之实执
了知怨敌伤害之正量
皆是嗔恨无处觅不同
安立名言之量心不安
比量之理依于现量生
判断现量真假依比量
犹如观待其子说父有
安立名言之量心不安
如理观察依于大乘义
大乘宗义依于正理成
若能自主无需随他转
倘若无法自主该信谁
正理源自了义圣教理
了不了义无垢正理断
理若能断何须寻了义
理不能断了义无处寻
无著眼中弥勒现为狗
不加观察俱生心难信
中观唯识堪布之见地
相违之处学者亦难信
若随普通世人求真理
获得衰败根因俱生执
若随世俗学者求真理
获得遍计执著更恶劣
有无是非真假等所诤
此消彼长弥漫此世间
常把所见看成是所知
亦将常识当作是正量
众口铄金遂信以为真
众口一词便开宗立派
一人心中自有一“正量”
其后更有“金刚之教理”
一山之中便有一宗教
聚集贤愚随从数千众
宣扬此教真实无欺惑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者
同门之人自然示欣喜
说与他宗难免遭唾弃
相异六道有情轮回国
悦意者十不悦意者百
人之所见天人不能见
真假正量法令由谁断
穷尽一生勤研学问之
宗派堪布难免无错乱
世间愚者虚妄之显现
取信名言之量定是错
所求所好心中诸显现
放置一边谓之为正量
乾达婆城消散旷野上
何似又得虚幻之珍宝
面容稍变显现便会变
镜子稍变显现亦会变
无常变化所知之显现
究竟观察必定悉消泯
对针仅作观察心生无
指尖针尖相遇心生有
手指现量感受以为有
显现可能迷乱以为无
遍寻有之根本以为无
见着无之尖角以为有
撒下实有之种能知假
感受虚假之果以为真
中观宗说的“没有承许”并非是说中观师终生缄口不语。尽管月称论师也曾作过:“这是那烂陀寺。我是月称。这是我的袈裟。佛陀皆由菩萨出。”等承许,但是对此,我们还是要区分胜义观察时和世俗观察时。(慈师说根大师此处所说的和麦彭仁波切的意趣完全一致。龙钦巴尊者也在其《如意宝藏论》中也很明确地说对中观宗的“没有承许”要加以胜义观察时和世俗观察时的区分。抉择胜义时,要说没有承许;而世俗观察时,也就是后得位时,要以他方承许的方式承许之。如果在后得位时,不作他方承许,那么基中观和道中观就无法成立了,这样一来,果中观就根本无法证得。麦彭仁波切也用稍微不一样的名相去说这个意思,比如在其《辩答日光疏》中用“以胜义观察为准时”和《定解宝灯论》中用“依据胜义观察时”去说要区分胜义观察时和世俗观察时。)有人说胜义观察时所说的“没有承许”本身就是一种承许;他们说这好比是某人说:“睡觉了,请别讲话”。这句话本身成了说话者不想睡觉的证据。这种类比根本毫无意义,可笑至极,很像下面这则群鹤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一群鹤在空中飞,领头的鹤跟大伙儿说:“别出声,否则会被射杀。”群鹤听后,回应道:“不出声,不出声......”,回应声此起彼伏,尘嚣甚上。
(慈师说月称论师指出自宗指的是圣者入定位时和胜义观察智慧所量的法性。麦彭仁波切也说中观的究竟因如是抉择义即是自宗。除此而外的所有世俗所知,名言所诠的种种,以及前六识的所有显现都是他宗。“我依世俗说,故是依他许,并非自方许。”此处,月称论师将依世俗和他宗安立成同一个概念;麦彭仁波切说月称论师所说的自宗,在后得位时,可以和世俗是一个概念。比如,月称论师出定后,后得位时所见的如幻的世俗显现是世俗宗派所承许的。月称论师入定位时,无一法承许,胜义观察时的净见量便是中观自宗,而世俗庸俗量是他宗。因此,自他相续中所有的世俗心都是他宗。根据这个见解,月称论师说,他是不会自方承认数论外道的任何观点,仅依他而承许。“仅依他承许”是需要的。有些人会比较极端,说这个“仅依他承许”也不要了,因为胜义观察时,无一法承许故。《中观精要讲记》音频19:慈师强调不能这样说,因为承认“仅依他承许”不仅没有过失,反而是需要的。在此,他引证了龙树菩萨的教证:“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月称论师也说:“随顺彼,正是为了知彼。”)
总而言之,对斋戒禁语的誓词和无记十四问,佛陀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如果承许这些是合理的,那么“没有承许”的见解也是合理的。《中观根本慧》十一品观本际品中云:“大圣之所说, 本际不可得。”《律本事》中云:“无应答是所有失败中最彻底的失败”,有些人就拿这个理来说事儿:“这样一来,“不作回应”的佛陀岂不输尽天下?”对此他们自鸣得意,实则是不明白个中深义。
圣天菩萨如此赞颂佛陀的一默如雷:
是故如此甚深法,
不与非器众生说,
是故智者皆了知,
佛陀即是正遍知。
如果自己明白了,“没有承许”的这个正见其实就会在自相续中生起。以前,给孤独须达多长者诚心祈请世尊驾临舍卫城接受其供养,为此,他可以建造祇园精舍供养僧众,对此世尊默然不语,而长者知道世尊已然接受他的请求。对此,我们都无法理解,更遑论明白世尊关于不语禁戒的甚深意趣?
(这一段,在白马旺杰先生翻译的版本里面缺了。不知道是没有翻译,还是排版时漏了。)因此,说“没有承许”的那个时候,那是胜义观察时。把“没有承许”当成有法,进行有无观察之时,就在世俗观察时里了。在世俗观察时中,佛陀除了说“世间凡说有无,我亦说有无”以外,还能怎么办?
娘绒(今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布鲁曼是十九世纪康区历史上出现的一代枭雄,能征善战,性情暴戾,以至于当时人人谈“布”色变。
某日,有人对布鲁曼说:“您是位转轮王。”
布鲁曼问道:“这是你的肺腑之言,还是恭维之词呢?”
那人说:“不是恭维,是肺腑之言。”
其实那人除了这般回应,别无选择。事实上,这番话是言不由衷的,对布鲁曼的畏惧促使他这么说。像那人的言不由衷一般,我们对火的能烧,水的能湿,风的能动等这些外境上的功用,也只能不由自主地去承认,尽管如此,于自宗还是需要有“没有承许”的简别。
这方面的阐述见于宗喀巴大师与他的上师仁达瓦之间的问答录,希望大家能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去研读。(《中观精要讲记》音频第20条/17分50秒开始。慈师说宗大师在给仁达瓦大师的信里面说:“要说承许,但是此承许千万不能说成是应成派的自方承许。所承许的是依他方而承许的。”这是宗大师最究竟的中观见。藏传前译后译之间相互理论时,宗大师的一些门人按他们的理解对宗大师的中观见进行的诠释不是宗大师甚深的究竟的中观意趣。后译(格鲁派)里一些正直的格西会诚恳地说要明白宗大师真正的中观意趣着实很难。慈师说宗大师在其诸多论释当中阐释过前译后译的各种论述。其中,有些是随顺外道而说的不共的论述;有些是契合前译的论述;比如,宗大师在论述大悲心时,他把萨迦派道果里大悲心的各种论述汇集归纳起来,并以噶举派论述般若的方式进行宣说。宗大师对其四大心子之一的共茹·坚赞桑波所宣说的中观见正是觉囊派的他空中观见。之后,贾曹杰指责坚赞桑波:“宗大师其他亲传弟子中没有人说他空见,你为什么要去说他空见?”坚赞桑波回答道:“我不知道其他人为什么不说,但宗大师给我讲的正是他空见。”另外,格鲁派里面也有人说宗大师文集里的《答·妙药甘露鬘》是宁玛派杜撰的,并非宗大师所造。但当问及宗大师亲造的《妙药甘露鬘》在哪里时,他们竟无言以对。不管怎么样,《答·妙药甘露鬘》还是收录在宗大师的文集里面。麦彭仁波切也说:“所斥责的是宗派偏见,而非佛法正见。他们不应该把前译和后译一分为二地去看待宗大师的意趣,而其他宗派的人也不应该去破斥宗大师的意趣。”)
这么一来,凡夫分别念里的所有思量,直戳其根本,无一例外地都是贪嗔痴使然。姑且说我们能所二取的心里真有个所谓的正理,那么自无始以来,我们在轮回中流转无数劫,串习这个“正理”如此之久,却不见丝毫长进,也可谓是奇事一桩。
对外境诸相产生的分别感受,猫狗只能用几种不同的叫声去表达。相比获得自在的菩萨们,我们的认知力其实还远不及猫狗;即便如此,我们企图用自己极其有限的分别念,以“无遮”和“非遮”等方式,去揣度遍智观照下的浩如虚空的离边法性,这无疑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没有承许”本身就是一种“承许”的说法和前面提到的“藏北牧民和甜味的故事”有相似之处。在过去藏北牧民的世界里,凡是带甜味的食物不是牛奶就是奶酪,糖这种东西也从未在他们的世界里出现过,所以他们会不由自主地认为糖本身和牛奶就是同一个东西。镜子的大小决定了镜中所显影像的大小,而将超出它范畴的一切承许为理所破,这种做法无异于是在自塞悟门,知道这一点很重要。
若是将心里什么都不承许,但嘴上承许诸多论述的立论者的立宗说成是心口不一的谎言,那么心里的实执感丝毫未减的驳论者所作的万法不实有的驳论也岂不成了谎言?我们遇到的人,方方面面都跟自己不同,因此,与他们交往时,聪明的我们知道要察言观色、口是心非,以便趋利避害。我们凡夫处理世俗之事尚且如此,更何况普度众生的佛陀,尽管其智慧功德早已超越十地菩萨,但他深知凡夫分别念无尽,根器参差不齐,因此他的究竟意趣和度众的善巧方便之间存在差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何谓正见?瑜伽师们说是“无可言思般若度,各别自证智行境”;而世间学者们,不管他们是否明白法界等到底是什么,却执持“非有即无,非无即有”这样的观念,硬要把它纳入有无之境,因为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被成为誉满世间的学者。法之界、学者之美誉、无改之自性、寻思之理、难已明了之离戏、易于理解之四边等,都只不过是他们表达各自的主张时,选来应景用的词汇而已。
总的来说,诸如刹那连成劫波、微尘组成世界等这些论述,到了究竟果位时,将顿时浑然一味。子光明和清晰明亮的显现彼此观待而证悟的空性智慧和母光明(基光明),一异,有无等一切将变成双面金刚亥母之一体——究竟的母子光明,以不再退转的方式相会,这正是解脱的果位。
比方说经院里的辨论,
驳论者:须弥山应高八万四千由旬?
立论者:承许。
驳论者:极微应无方?
立论者:承许。
驳论者发太过:按照你所承许,那么,一尘之上应不可安立与无量世界的无量尘数相等的所有世界,因为具八万四千由旬的须弥山不能被无方微尘所容纳之故。(慈师说此处根大师的引证是《入中论·自释》里的这首偈子:“此清净行随欲转,尽空世界现一尘,一尘遍于无边界,世界不细尘不粗。”)
立论者:仅就目前共许的这个特别法而言。
如果可以这样安立特别法的话,那岂不成了“非非有”应成“无”的道理?这样一来,也可以说因为需要正确理解无遮、非遮的原因,便对诸如此类的观察因给予特殊的回答,也并无任何不妥之处。
简言之,信受大乘的一切也应该信受它的不可思议之处,否则,在善于推理的逻辑学者们看来,密续中描述的在极热劫火之中央,日轮之下,于极清凉澄澈白月莲花垫之上端坐,与极爱佛母相拥的这些诸佛菩萨看似有悖常理的境相,自然是处处自相矛盾。他们也会因此说这些不过是显现方式而已,实则与唐卡上画的画毫无区别。但是,需要明白,这些都是将能所、贪嗔、冷热、净秽等二元分别融为无二一体的双运智慧之身,或身心合为一个本体的双运之身。
如果说佛陀的报化二身仅仅是为利他而示现,他的三十二相和八十随好也主要是为了让人心生喜悦的话,那怎么可能在这个福慧二资粮圆满究竟的具备一切相好庄严的报身上再出现个猪面或狮面呢?
大乘,特别是金刚乘,要求你修视师如佛,进而逐步将自己观想为金刚持,身体观修成为圆满的坛城,并对此深信不疑,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颠覆当下的这个所谓的“正量”。
以五肉、五甘露向佛陀献供等,都是为摧毁凡夫的分别念和逻辑思维。与此相反,向殊胜的对境供养不净物的这个做法,与“正量”,特别是逻辑推理,尤其是世间律令相违。因此,希卫沃殿下(寂光王,十一世纪中期,西藏阿里古格王朝的一位国王,是位出家人)说到:“不净淤泥供养诸如来,悲悯腐尸潭中诸有情。”这不正是如他所言吗?
总之,我们要明白,视不净为净、无理为理等,都是为了破除凡夫的分别念而宣说的。终有一天,我们会获得一个无上的远离二元矛盾的果位——在那里,地大即是佛眼佛母,佛眼佛母即是地大,主尊即是眷属,眷属即是主尊。(慈师说这个在《续部·幻网经》中有讲。《中观精要》音频23条/8分25秒)
我们的毛病里头,有这么一个突出的问题:在我们可以语言无碍表达、内心完全通达世俗胜义二谛之前,只能坚持长期的闻思修。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倾向于倚重易于言说的理论部分,当产生与之相应的一个分别念时,我们会自以为,依靠教证和理证,找到了一个究竟真理,但实际上,这只不过就像“好肉者找到了肉,好酒者找到了酒”一般,找到的只是与自己分别念相匹配的一个对境性的东西而已,而绝不会是菩萨们的甚深行境。
佛陀洞悉凡夫的心,深知要使其明白究竟的本性,需从破、非和无的方面切入,除此而外,若从立、是和有的方面切入,欲将凡夫引入实相,是行不通的,所以凡是他方承许的都以应成因遮破,而自宗没有任何承许,这正是佛陀所宣说的法之心要——彰显圣法本身的无住无境。
正道的最大障碍是分别念,对此,法称论师云:“灭除分别妄想网,甚深广大游舞体......”;陈那论师也云:“若以分别见法性,如来圣道终不见。”为诠此义,《释量论》自义比量品中云:“法有法建立,如异非异等,是不观实性,如世间所许。唯依如是许,遍立能所立,为入胜义故,诸智者所作。”
你们(格鲁派)说因为胜义中无,所以这个“无”不能抉择它为毕竟无,但因为世俗中有,所以这个“有”能抉择它是毕竟有,这个说法无疑是在说,因为圣者的智慧没找到它,所以它无法承当“没找到”,而凡夫的分别念找到了它,所以它能承当“找到了”。除了根本不可能是空基有法的于胜义中无的“自性实有”和“兔角”以外,如果因为任何时候于胜义中无的缘故而无法找到那个堪能承当的“无”,那么这个“无”不能承当“无”,但这个“有”能承当“有”。
对“兔角于胜义中无”这个所破假以胜义简别时,能引申出“世俗中有”,不然,“兔角于胜义中无”和“兔角无”这两个名相在表述作用上的差别从何体现呢?鉴于此,月称论师在《显句论》说:“拿‘自生于胜义中无’这个理去遮破数论派时,虽然在此假以胜义简别,但是因为外道不承认二谛,遮破时要分开二谛,所以对外道是不需要假以胜义简别。”因此,如果遮破“于二谛中皆无的兔角”,是不需要假以胜义简别的。“兔角于胜义中无”和“证悟‘兔角于胜义中无’的心”是否就是空性和证悟空性的心呢?证悟“根本就没有兔角”的这个心,可以间接地破除有黑白兔角的增益,因此也可以破除兔角实有的增益。
烦恼作为道所破时,其实根本没有一个实有的所断,因此,不需要假以胜义的简别。当说兔子头上有个尖而长的黑色犄角时,可以问问为什么能在本无的兔角上安立所谓尖、长等差别法,但却不能安立“兔子头上没有实有的兔角”的胜义简别呢?(《中观精要·讲记》音频24/2分13秒。慈师说格鲁派提出不能给兔角安立胜义的简别。为什么?因为说胜义无时,会被理解成世俗有。)
道所破的这个烦恼心,它前前的执著都是后后的能坏,因此说它不需要安立胜义简别的话,那理所破要来干嘛呢?(《中观精要·讲记》音频24/7分。慈师说道所破和理所破要相辅相成。两个所破要做的是要把那个如幻的显现也破掉。)
章嘉仁波切说:“将实执中有的和实执前可见的这些法弃置不顾,而去遮破另一个东西,就好比是放着明晃晃的显现不理不睬,反而去找个压根儿不存在兔角来破。”
嘉木漾尊者曾向居钦∙桑杰嘉措大师问及应成自续两派见解上的差别时,大师伸手指着寝室里的一根柱子说:“自续派认为眼前这个赤裸裸显现的东西就是柱子,而应成派则认为这只是柱子的施设处,在它上面只有个有名无实的柱子而已。”
唯芒班智达拜谒阿热大格西时也有类似的对话:
阿热大格西:“五部大论,你精通哪部?”
唯芒班智达:“比较熟悉中观。”
阿热大格西指着跟前的一张桌子问:“应成派认为这是什么?”
唯芒班智达:“桌子。”
阿热大格西:“不应成桌子,因为仅是桌子的施设处之故。”
对此问,唯芒班智达仅无言以对。
上面这二则对话正是应成自续两派见解的关要。
因此,将眼前这个四方形的木制品执为桌子,是应成派所说的实执和自续派所说的名言量,对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同样地,我们也要知道,说眼前这个四方形的木制品是桌子,是应成派的他方承许和自续派的自方承许。因此,被问及眼前这个是否是四方形时,要知道这是四方形的施设处,而不是四方形。
因此,眼前的这个“有”是“有的施设处而”不是“有”,或者说仅仅是后后的施设处欺骗了前前的施设处;没有承许的施设处和施设法二者皆空,因此,好的离戏和坏的无遮就成了表达同一个意思的异名,殊途同归——这正是斩断轮回之根的道之关隘。尽管如此,庸俗认知尚未转变的世间普通人会异口同声地说:眼前有的这个东西上有个四方形的木板,这个四方形的木板上有张桌子,桌子上有个瓶子,等等。说世俗普通人的这个俱生我执是否受了宗派思想的影响,这个界限其实极难划分清楚。这里可以列举一个情形说明:很多目不识丁的普通人会随大流地相信“金曜日诸事皆宜”的说法,这种从众的观念可以断定是被宗派给洗脑了。诚然,认知是否已被宗派改变,可以通过法的实相去区分,但在此,我们引述宗大师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因为缘起,中观宗承许自性无,而他宗却因此承许自性有,这二者其实都属于宗派见。”总之,依据比量的一切都是宗派,依据现量的一切都是普通人与生俱来的认知,只能这样来区分,因为见不到任何能区分的法。
这样一来,五蕴聚合的对境执为“我”是俱生无明的“我”,而这个具有常、一、周遍三大特性的“我”则是受宗派遍计影响的遍计无明的“我”,这是对俱生我执和遍计我执的一种区分方式;但也可以作如下的区分:“不观待名言安立,执独立客观存在的外境”是所有众生的相续里面,四大以自性的方式形成的俱生无明,而“不实有,但执自性有”是清辩论师建立的宗派观点作用下形成的遍计无明。由此可见,俱生、遍计二无明之间的差别很难区分得清楚。
小孩子随地大小便是俱生执著。随着父母观念的影响,当有一天他们知道自己不能再随地大小便时,这难道不就成了遍计执著吗?
总之,这世上,还未受到佛教四大宗派以及其他外道宗派影响的可能大有人在,但是没有被自己的三观所影响的人,一个都不会有。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的三观是父母等周遭人的教育观念,成长的环境和自己的认知力相结合的产物。
中观应成派的论师们因为不见如梦如幻的显现——安立世俗之基,因此,他们只是随顺性地将世间名言共称安立为世俗谛。
因此,就无误的显现而言,人、鬼和狗,各有各的无误的显现。以房子的显现为例,如果说人和鬼各自心前显现的房子都是正量所成,而且承许有一个产生这两种显现共同的基,即一栋即非人所见也非鬼所见的房子的话,那么这种说法和数论派所承许的有个共同的恒常的实有的法就没区别了。(《中观精要·讲记》音频25/17分21秒。慈师说这是宗大师的《入中论·善显密意疏》中的说法:承许有共通显现时,六道有情的识都安立为正量。)这种说法和唯识宗的说法也有点儿相似,但瑜伽行派的行人们不承认六道有情有一个产生共同可见的显现的基,也就是六道有情心前没有共同显现的一碗水。唯识宗认为,根本而言,六道有情心前显现的外境只不过是六道众生各自的分别识产生的现基阿赖耶识上存储的习气又被唤醒了而已。
诗云:
异熟六身六道诸有情,
生起六种显现不待言。
具备六根人道之身体,
无有共同之基六显现。
总之,那些在我们凡夫面前显现的,可以用“七相木马因”拆分成千万个碎片,但这个显现不会因此产生丝毫的改变,这个被认为是所知障或它的一种作用。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凡夫是无法看到墙背面的东西,而佛陀可以清晰地看到,因此,以胜义理破除认为显现的实有属于断除烦恼障,而破除串习空性后虽不会再执著外境实有但仍有无分别识的显现属于断除所知障。(《中观精要·讲记》音频27条/1分21秒:慈师说这根大师这里的说法很像格鲁派的说法:宗大师说凡实有皆烦恼障,因此以理明白万法不实有,就可以断除烦恼障。但慈师说,因为以理初步明白既不是见道也不是修道,所以仅凭这个实际上是无法断除烦恼障的。宁玛派自宗说以胜义理破除时,凡以胜义理未破除的实有不能都说成是烦恼障。自宗认为人我执是四边里面的有边,所以是烦恼障。以胜义理遮破实有谓之理破,也就是能以理明白实有其实不实有。虽然这个明白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修证,但是在说理所破时,这样安立其实也不是不可以。格鲁派说凡实有皆烦恼障,堪忍胜义观察,所以凡实有都是烦恼障。)月称论师说断尽二障的佛陀没有这般显现。
打心里认为见到了桌子是烦恼障,而仅仅是眼睛见到桌子属于所知障。(《中观精要·讲记》音频27条/6分37秒:慈师说根大师这个说法也跟格鲁派的很像。宁玛自宗不认为桌子实有是烦恼障。)寂天菩萨也说:观看幻术表演的观众贪著幻女的方式是烦恼障,而幻术师自己贪著幻女的方式是所知障。
在灭除了非此即彼的分别妄想网的彼岸,是一异合一、远离思境、周遍一异的甚深广大游舞体。无论上智下愚,普贤圣慧之光芒,应机普照有情无有尽,对此我深信不疑,故顶礼。(藏传习惯在偈子的前后补充词句,将其蕴含的意义诠释出来,比如全知麦彭仁波切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释义》、《量理宝藏论释》等就是以这个方式进行注解的。这段便是以这种方式对皈依法身偈子作的解释。皈依法身偈子原文:灭除分别妄想网,甚深广大游舞体,普贤圣慧之光芒,普照有情故顶礼。)
因为证悟诸法无自性时,证悟者和未证悟者二者心前显现的山河大地将迥然不同,所以二者口中所谓的山河大地其指向也不同——未证悟者所说的山河大地指向的是实有的山河大地,而证悟者自己承许的山河大地指向的则是非自性成立的山河大地,因此非自性成就不是山河大地和是山河大地就一定是非自性成这两种想法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达成共识的基础。
中观应成派和有实宗之间没有共同显现的有法,即便有,也只是为了便于相互交流沟通而已。比如,相互完全陌生的一位汉人和一位印度人同时高呼“国王万岁”时,汉人心中显现的是身披龙袍、长髯飘逸的帝王之相,而印度人心里显现的却是身着白袍,脸无胡须的国王之相。虽然,此时“国王”这个词达成了一致,但究其原因,不过是为了避免争论而达成的共识而已。
事实上,说心里承许也好,嘴上承许也罢,凡是按照自己的显现去如是承许,并对此深信不疑的,叫自方承许,而显现和实相不一致的承许叫他方承许。在如幻的显现上,对显现的四圣谛和五道等作出的承许,实际上,是对幻相的承许。但是,若不依这个虚幻的次第,趋入究竟法道便无处可寻了。对此,寂天菩萨在《入菩萨行论·智慧品》中说:“为息灭众苦,不应舍果痴。”对佛果的痴心一片如同苦海上的渡舟,一旦抵达轮回海的彼岸,它便会与轮回一道,被永远地抛弃。
顺着第一个台阶,可以走到第二个台,到了第二个台阶,第一个台阶自然就被弃于脚下了。以此类推,下下上所依,上上而弃下。孩童时有的那些无知幼稚的观念若未被改变的话,后面壮年和老年时的成熟将无从谈起?同样地,如果凡夫分别的习气没有发生改变的话,趣入佛地岂不成了镜花水月。
有实宗以“无自性则因果不合理”向中观应成派发出太过。中观应成派回答道:“无自性没有'什么都无'的过失”,这个所谓的应成派的回答是后译中观派的说法,而“因为自宗对自性的有无和是非等一概不承许,故无过失”才是前译中观派的观点。
有实宗(《中观精要·讲记》音频28条/8分06秒:慈师说一般而言,唯识宗以下的宗派是有实宗,而格鲁派将自续派也安立为有实宗。)拿着“破有之因”去成立“无”,拿着“破无之因”去成立“有”,认为否定一方就必定成立另一方。应成派不仅无余遮破他方,而且连自方拿来遮破他方的因也一并遮破,这正是中观宗不共的主要特点之一。龙树菩萨在《中观根本慧论·观来去品》中说:“已去未有去”:在已经去过的路上没有去的行为。那么在未去的路上是否会有去的行为呢?未去的路上也没有去的行为。那么除开已去和未去,是否在其他的时间和道路上,比如正去时,还会有去的行为吗?“除已去未去,正去非所知”,这句偈子遮破正去时有去的行为。
入定时“无法可见”的空性和后得位时“如幻的显现”,这二者一旦关联起来就是显空双运的意思。我们要明白于胜义中什么都不成立而于世俗名言中什么都可以成立的意思。
藏传前译派将无自性承许为人无我,将离四边戏论承许为法无我。而在后译派看来,二无我应该从空基有法去加以区分。他们承许瓶子和柱子无自性是这两种有法的空性,因此,补特伽罗的我和我所无自性是人无我,而瓶子无自性是法无我。藏传前译派认为,证悟人无我和法无我这两种见解之间的高低差别其实很大:将住在实有存在的这个分别念的反体上的心(万法非实有)安立为人无我,但这个实际上还是没有离开意识的范畴。世俗中显现的万法,无论在意识层面弄得再细致,终究还是有、无、二俱和非二俱这四边里面的戏论。因此,这个所谓的离开四边的清净心的胜义,归根结底,指的是不可言说的胜义。
《入菩萨行论·智慧品》中云:“胜义非心境,说心是世俗。”“若实无实法,悉不住心前,彼时无余相,无缘最寂灭。”龙树菩萨的《王谭宝鬘》中云(丹珠尔本生部111页A面):“彼时圣法无境。”也云:“佛法无住。”这些都表明如来教法的殊胜之处在于它跟外道的那个根本性的差别:它不停滞于轮回世间分别念的对境上的有无,更没有迎合它而去建立一个与之相应的分别念宗派的方便之道,而是明明白白地指出了一条超越分别念樊篱的出世间的方便之道。
当然,我们也会听到其他一些关于如何趋入佛法的看似深奥的言论,但实际上,那些只不过是现量和比量之因粉饰下的俱生心造作的口舌之能而已,无疑会使轮回的根扎得更深更牢固。宗喀巴大师也曾说:“尽管你依止佛法很久了,但因违背了佛陀的教法,你的精进修持,只能使你的我执变得愈发坚固。 ”我们要明白宗喀巴大师说这番话的良苦用心。
“无可言说本身就是一种言说”的争论其实是凡夫的分别念相互认同的一种表征,就像患了胆病的人们把白海螺执为黄海螺一般。患了胆病的立论者和驳论者之间的辩论和能做梦并认为所梦是假的心很像:只要胆病没好,梦没醒,那么就会不由自主地落入非此即彼的二元争论的泥沼中。我们要明白这既是无明的过患,也是缘起的功德。
有实宗驳斥“没有承许”的逻辑是这样的:一般说来,如果说只要开口说话就算是承许的话,那么立论者没开口说话,驳论者就不可能反驳,因此,“没有承许”其实就变成了一种不可能,所以也就没有遮破的必要了;有的话,所谓没有承许和不说话就变成有承许和说话了,这样一来,所作的“没有承许”就恰恰成了有承许。
“没有承许”本身是“似能破”这个争论是中观应成派和有实宗之间展开的。事实上,在有实宗看来,“无自性”这个词本身也具有自性,因此“诸法无自性”属于“似能破”;有实宗所说的“一切都没有自性的话,那么你所说的‘无自性'这个词也应该没有自性”和“没有承许本身就是承许”二者所作的反驳其实没有差别。龙树菩萨说:“何谓无承许,即是汝所许;何谓黄海螺,即是汝所许。“
所谓承许,顾名思义,说者为诠释所诠义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必须是说者自心深信不疑的。如果承许这样的说法,那么佛陀就不可能宣说不了义,凡夫也不可能撒谎了。总之,不对各种现象、情况、说法、想法和宗旨加以简别的话,连对佛法生起基本的信心都很难。因此,佛经所说的“若诸根是量,圣道复益谁。”也可以说成是“若我能断之,圣道复益谁。”
先成立“导师”为量士夫,尔后再依教奉行,这是外道的做法。先以正量成立佛陀所宣说的教证,然后再成立佛陀是量士夫、正理王,这是内道的做法;是否依止佛陀和奉行他的教法仅仅是针对三所量里最极隐秘分而说的。那么,何谓依教奉行无有欺惑呢?一般而言,所谓的有无欺惑,是追随某人或某种观念时,根据随之而来的利益或损失来进行判定的。关于遵循佛陀所宣说的辨别善恶之法并对此深信不疑,圣天菩萨在《四百论·破见品》中说:“佛说隐蔽法,于此若生疑,可依无相空,而生决定信。”判断任何教义是否圆融自洽,主要看其核心思想,观一隅而知全貌,核心思想准确了,那围绕这个核心展开的整个教法体系就不会有错。佛法的核心思想是佛陀所宣说的空性,它是万法的实相,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由此,可以确定佛陀所宣说的关于世间人天乘的论述也是不会有错谬和欺诳的,所以依止佛陀并依教奉行只有百利而无一害。这跟母亲要孩子听话的例子有相似之处:母亲告诉孩子外面有老虎,或者跑去外面的话要割耳朵,对这些话无需加以了不了义的观察,因为母亲这样说的目的不是为了孩子不跑出去,而是为了让孩子相信她,进而听她的话,孩子自然会因此而获益。
佛陀说:“(比丘)不可如娼妇般行非梵行。不可如新娘般涂脂抹香装饰自己。不可像在家俗人那般将僧裙扎得高高的。过河或被人侵犯时,则可以要把内裙提至膝盖处。除此而外,应该将内群下放至脚踝处。”从如此细微的律仪到万法的究竟实相,佛陀的善巧周遍于一切。我们要把佛陀宣说的教法两两分开——随顺世俗而说的法和佛陀的本意。佛制戒所缘六群比丘的僧裙要系得高过膝盖还是要往下放至脚后跟处,在佛陀那里其实本无差别。他为出家众制定那样的戒律,是为了让舍卫城里在家男女众不对出家众生起不清净的分别念。同样,“虚空虽无边际却有中心,轮回虽无开始却有终点......”等也都是佛陀随顺三界轮回和舍卫城中的凡夫和在家众的根基而宣说的。
在世俗显现未灭之前,在识的所依未转变之前,尽管可以现量证悟空性,但仅因随顺世间,不得已要承许之前所承许的种种显现,对此不需要加以任何造作的以理观察。尽管此时做了承许,但对已经成为他方的现量的见闻觉知是不需要以理进行任何破立的。不承许世俗,便有堕入断见的过失的这个说法,仅仅是对眼耳所缘对境的有无进行破立而已,因此这类二元性的破立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嘴上说着什么都没有,但心里的执著却丝毫未得到改变的人,对他进行破立的必要性着实不大。比如,你去问一位没有承许的人那边是什么时,他一定会如此回答:“是山、是树、是人......”,因此,不需要想方设法依靠诸多道理让他做出如此的承许。
对魔术师而言,无中生有正是他要做的事儿。他凭空变出的大象,观众会信以为真,而且会好奇地问魔术师大象是真的吗?他当然会说是真的,而他这样说仅是他方承许。
总之,如果不承认关于了不了义的论述的话,也就无法区分关于自方承许和他方承许了。有人驳问中观宗:“中观论典的所诠,如果不是你们中观的自方承许,那又是哪宗哪派的呢?”对此可以这样回应:佛陀在《解深密义经》、《楞严经》等佛经中运用了大量的因去宣说没有外境义的阿赖耶和能所双亡的这个最究竟的空性义,所以这些如果不是佛陀的自方承许,又会是其他哪个宗派的呢?
因此,能真正妨害他方承许的这些因,实际上,很像之前提到的“布鲁曼是转轮王”的那个典故。试想,如果不加善巧,直接告诉娘绒王·布鲁曼因为出于恭维才跟他说了那番话,保不定有杀头的危险。因此,在布鲁曼跟前,只有将他方承许当作自方承许来说。这方面的阐述见于宗喀巴大师与他的上师仁达瓦之间的问答录。
如果没有他方承许的方便,那么在法性尽地灭尽一切显现的佛陀与二取显现中流转的众生之间就连支言半语都无法交流了。
如何区分世俗观察时和胜义观察时?胜义观察时是一种心的究竟的抉择方式,它对事物的本质进行观察,分析它们是否自性成立。世俗观察时仅对事物的显现进行观察和分析。不用说有实宗,就连那些未被宗派思想熏染的普通人都明白幻术里出现的金子没用,因为那是心捏造的假金子,他们想要的是自性有的真金子。想要自性有的真金子是对金子生起贪著的根,也是嗔、痴这两个实执无明烦恼的根。普通人所要的这个金子必须是他们认为究竟有的真金子,或者通过他们自己的“自性有的观察之理”获得的真金子。
不愿意承认自方承许和他方承许二者有别,说到底,与佛陀和众生的显现和所知应该无二无别其实是一个意思;如此一来,谁还会相信“力持菩萨”依靠神通也无法见到佛陀顶髻最顶点的这则教言呢?
按理说,相信佛法不就应该相信它的不可思议之处吗?把思维无法触及和观察的一切说成是“无”,在我看来,与反驳“没有看到并非无”时持的这个断见其实是一个指向。
如果没有火却有烟是需要量成的,为此需要眼见为实和我的眼见为实,但因为从未见过这样的事,因此,它可以证明有火就有烟是周遍成立的。这类理证方式无疑是管窥蠡测。它试图将所知的实相,即普贤法身的无量红白光中显现的无量的苦乐好坏的相,统统塞进逻辑理证的狭小的孔隙当中去加以观察。
月称论师在《入中论自释》第六品现前地品中说:“......为遮遣世俗而精勤修行。”对此,宗喀巴大师说:“无需为遮遣世俗法而苦修。”因此,可以这样去理解,努力修道到达究竟时,显现的一切会全部消失,所以,对世俗的各种承许,总的来讲,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一种承许。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从俱生无明中产生这些现象是不由自主的,同样,以遍计无明为根本建立的善恶、有无等二元认知也是不由自主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六道众生只能不由自主地流转于三界轮回之中。因此,不由自主的承许就应该理解为不由自主。
那么,应该对“需要不由自主的承许”生起悲心,而不是欢喜心。月称论师在《入中论自释》第六品现前地中说:“我们为了遣除世俗法而精勤修行......如果您没被世俗所败,我也会敬仰您、跟随您,成为您的朋友。”
小势力会被大势力所坏,对此,寂天菩萨在《入菩萨行论·智慧品》中说:“.......为上上所破(索师翻译为:层层更超胜)。”也即,世俗观察因被胜义观察因遮破;而胜义观察因而言,瑜伽师的见解也是上上宗遮破下下宗。仅仅由于身不由己和势力大,就可以构成的妨害的话,那么烦恼五毒,特别是凡夫相续中势力最大的无明,它们麾下的分别所缘的耽著境就应该被承许为合理。为举例说明“下下的见解不妨害上上的见解”,寂天菩萨在《入菩萨行论·智慧品》中发太过说:“.....否则见垢女,有违世人见。”
因此,有实宗认为,以理遮破外境等世俗法时,只能说是理不可得,并非是将其遮破。彼宗(格鲁派)及其彼宗之理不可证得的外境不会变成为无,而实有和“自性有”于应成派的胜义理没找到,所以是存在的,故破之,这种做法实属稀奇。
如此承许时, 若将觉囊派的他空中观也归为学者们思维的产物,它显然属于世俗法的范畴,但是仅仅因为有无等有境分别念没找到,怎么能去说找到了“无”呢?总之,仅就世间名言的角度来说,只能把没找到或根本找不到就当作无,因为有无之间的界限没有了;但如果因此认为没找到就是无的终极所指,那么就自塞悟门了。
虽然“现而不可得”是无的究竟能立之因,但划定能现多少和不能现多少的界限是极其困难的。比如,佛经中说,一个具有神通的人,因为看到房间里没毕舍遮(食肉罗刹),即现而不可得,所以确定没有毕舍遮;而神通力更大的登地圣者可以在马车车轮大小的空间里看见与整个大地尘数等量的有情众生。因此,应该是依据神通或证量的差别来区分能显的多少。如果说“现而不得因”是沧海,那么千百万凡夫异口同声认定的这个“现而不可得”,充其量,也顶多是沧海一粟;同理,要明白那个思维所建立的无,也只是无的一个微乎其微的部分而已。
如果说遮破所破时,对其不加以实有的简别,就会变成断见的话,那么遮破实有时,不加以自性的简别,也一定会变成断见。无始以来,一直无法成立这么一个实有的简别,但现在却安立一个新的实有的简别,然后对其进行遮破,这个做法无异于拿着箭不去射本来就有的靶子,反而重新立个新的靶子再去射。无始以来,一直就不知道怎么对瓶子加以实有的简别,就算现在学了,谁又能学会呢?
在世俗中安立的胜义谛非真胜义,因为真胜义远离戏论。以戏论的方式建立真胜义就是于世俗心前建立的胜义,即在未被迷乱因染着的无垢心识前所安立的相似胜义。印、藏两地和前译、后译两派的所有智者,对将这个世俗心假立的相似胜义承许为世俗谛应该是一致首肯的。
总之,虽理能破之,但仍无法对此生起信心的话,这根本不可能是中观宗,更不可能是应成派。所破之量或理本身就可以遮破它能遮破的一切,因此知道兔角本无的那个心根本不可能把兔头给遮破了,故对所破的抉择不需要如此的谨小慎微。
没有谁会承认自宗是自相矛盾的,比如,承许因中有果而不见果的数论派,承许能所一性而外境能显的唯识宗,观察时无而不观察时有的中观宗等都是如此。这些宗派的这些承许都是企图依靠文字语言来统一矛盾的宗派学说而已。矛盾具有一体两面的特性:特性一是指把绝对无法同时并存的相违的两个东西编排在一起(矛盾的对立性),特性二是把绝对相违的两个东西以不相违的方式让它们同时并存(矛盾的统一性),因此,宗派们的这种欲盖“统一”弥彰”的做法其实是在凸显它们承许上的自相矛盾。从矛盾的统一性推导出来的“非无不成为有、非有不成为无”等等这些矛盾都是在中观师那里出现的问题。这些不仅于世间普通人而言是矛盾,于中观宗而言,也必须承许它们是矛盾,不过仅仅是他方承许而已,换句话说,也就是于世俗承许他们是矛盾的意思。
宗喀巴大师的宗旨是:色法等虽于诸根识前有,但如是显现的有本无,即于名言中不承许有自相。
尽管以胜义观察因遮破而确定为“无”的做法和以世俗因遮破后执为“无”的做法相似,但二者有本质上的差异。通过胜义因的观察,认为若“无自性”,即“本无”的心,它也知道“无”也“本无”,所以不会堕入断见。而认为没有因果缘起的心,却是按照另一套建立无的说法,也就是世俗认定“无”的说法,产生的;按照月称论师的意趣,承许世俗中的某些法“有”,尔后再去说其中的某些法“无”,这属于断见;如果知道这个“无”属于世俗范畴,那么远离四边戏论的胜义理所说的这个“无”就是离开有无二边的,对此,佛陀如此授记龙树菩萨:“......其名号曰龙,能坏有无边,.......如此阿阇黎,善说故希求。”
根本而言,找不到“法界”和“不可思议”,究其根本,主要不是因为太过于相信“有”,而是太过于不相信“无”了。若将同类凡夫从未找到的一切统统以我们认定“有”的方式归入“无”,那么佛陀的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和身意相融等诸功德也要纳入我们认为的“无”当中了。
这个所谓“有”的世界其实是被外面一个与它相对的“无”所框定出来的;比如,无火便无烟等周遍之理,事实上,就是在说所谓的“有”是被与其相对的一条“无”的绳索绑定出来的“有”,因此说破无边是诸因之中的究竟因;因此,世俗显现和世俗因的最极处,实际上,最终指向的也是这个“找不到”;如果无法超越它,佛陀就算历尽三大阿僧祇劫,勤修六度万行,也不可能到达彼岸。
全知果让巴的宗旨,概括起来讲:证悟“无实有”的是声缘乘的阿罗汉,而证悟离四边戏论的才是大乘菩萨。但是,果让巴大师又将格鲁派的“无遮”见说成是断见,这样一来,阿罗汉岂不依靠断见而证得了阿罗汉的果位,这实在是很稀奇。
一般而言,不论是研习显宗或是密续的哪部论典,会发现它们都在讲“以见解断除烦恼障,以方便断除所知障”,但是,如果因此对如何生起此二障的方式也加以区分的话,那就等于在犯糊涂了。
尽管所有智者承许无余清净了一切不清净显现的佛陀还能照见一切不清净的显现,但这一说法也应该区分自方所见和他方所见,否则不合理。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立论者指出白海螺不是黄海螺,患了胆病的驳论者对此予以反驳:眼前所见的颜色为有法,应成不是海螺的颜色,因为不是黄色之故。如果立论者对驳论者提出的周遍性及其所立的反体一概不予承许的话,那么这二位,一位患了胆病,另一位没有患胆病,就彻底丧失了对海螺进行辨析的基础。因此,立论者对驳论者所建立的这些承许——凡是海螺必定是黄海螺,凡是海螺的颜色必定周遍为黄色,因为不是黄色就不是海螺的颜色——首先要以他方承许的方式如是承许,尔后才去跟这位患胆病的驳论者讲无常、无实有、如幻等道理。因此,我们也要知道佛陀摄受凡夫也用了相同的方便。
患胆病和没患胆病的二人之间,是不可能有丝毫共同显现的法和有法,所以,他们之间关于所谓海螺的探讨和辨析,只能是在粗大的意识层面展开的,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进而对海螺的差别法进行探析,除此而外,要让胆病患者相信海螺实际上是白色的,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因为只要跟他提及海螺时,他心里现起的那个海螺就是黄色的,而以这个假立的黄海螺作为差别基,他的眼睛无缘现见白海螺,因此,只有通过闻思可在意识里现起的各种道理,以“渐”的方式让他明白海螺是白色的,除此而外,别无他法。
他方反驳中观应成派的“没有承许”时,会问龙树菩萨所造的开演中观思想的论典难道不是他自己宣说的?这跟问佛经中讲“有我”、“外境义”和“三乘究竟”实有成立等内容是不是佛陀自己宣说的其实并无差别。遮破实有要周遍于胜义和名言二谛,这一点宣说得十分清楚,因此,破四句生因也要在名言中去破。总之,在名言中无余遮破所有执著实有的极其细微的分别心之前,是丝毫不可能去遮破于胜义执著实有的心。
如果承许还有一种独立于自生和他生以外的生,就可以成为中观宗的话,那承许还有一种独立于一异以外的实有,为何不能算作是中观宗呢?因此,尽管实有的瓶柱无法堪忍破四边生这个胜义因的观察,但一个独立于四边生之外的如幻的瓶柱是存在的,这样一来,我们也可以说,尽管“实有”无法堪忍破四边生因的观察,但一个独立于四边生之外的如幻的实有是存在的,这个说法是极其荒谬。
如果公正地去分析宗派之间对堪忍观察和不堪忍观察的界定,就会明白如何界定也是因“宗”而异的:比如,自性、神我等是数论派的堪忍观察,瓶子以微尘实有等是有部和经部的堪忍观察,没有外境等是唯识宗的堪忍观察。(应成派)认为上述宗派的堪忍观察不究竟,所以去努力去成立阿赖耶不存在、外境义存在等观点。
所谓名言量,如果不是针对那些未受过任何宗派思想影响的普通老者们说的,那就应该是针对那些学识渊博的有部、经部和唯识宗等的宗派学者们说的,除此而外,还能针对谁呢?这世上,几乎没有谁生下来就什么都懂,都要经过后天的学习,既然是这样,可以确定地说,在学习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宗派思想的影响,因此,如果说还有些心识未曾受到过宗派思想影响,那就只能是那些阿猫阿狗的相续了。
受顺世派的影响,我们认为没有轮回,而受顺世派以外的其他宗派的影响,我们认为死后会再生;因此,除了“现在我生了,最后我会死”的这个朴素的想法是俱生的心识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任何一个未被宗派思想影响的遍计心识了。
以四句生因遮破实有的生,但仍然认为还有个“如幻的生”的话,那么破四句生因就成了世俗因,这样一来,四种生以外,还有第五种生,那样的话,以四种生作为边际条件对“实有生”进行遮破就毫无意义了。
按照实有生和如幻生,实有的瓶子和如幻的瓶子之间区分有无的方式,也能同样对实有和如幻的实有之间的有无差别进行区分。如果根本不去遮破如幻的生和有的话(理所破),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如幻的所知障和烦恼障也根本不会被遮破(道所破),这样一来,世间普通人的心识里面就无一法可破了。月称论师在《入中论自释·第六菩提心现前地品》中问的“汝所计生由何成?”这句被你们诠释为如幻生,这样的话,就要问问有实宗所承许的那个生到底是属于四边生里的哪一边呢?胜义因没有妨害世间愚者的认知,反而妨害了宗派宣说的理,这好比是说,白天看见东西但晚上看不见东西的人的眼识会被理所妨害,但与人眼情况相反的猫头鹰,它的眼识就不会被理所妨害。
总之,于心识的差别而言,上上的认知不妨害下下的认知,依据这个说法,是无法对“见所断”的诸烦恼能被见道摧伏和九品修惑的诸所断能被其对治法摧伏生起定解的。这样一来,可以说一切有部不共的各种观点是经部没找到,而不是没有;同理,唯识宗所说的阿赖耶也是中观宗没找到,而不是没有;诸如此类的说法过于随心所欲了。
有些人(格鲁派)认为要区分没找到和找到无二者的差别:因为眼识永远无法缘到声音,所以于世俗中不能去说眼识是否能缘取声音;耳识亦然。仅仅因为眼识没缘取到声音的缘故,就说是声音没有的话,那么因为山河大地等也无法缘到色法、声音和实有等任何一法,所以说它们已经获得了最究竟的殊胜菩提的果位了。
另外,依据这样的说法,也可以说颠倒识和正量互不妨害,由此可以进一步去说,有些人认为有烟的地方没有火这个颠倒识,只是没有看到火,而不是找到了一个叫没有火的东西。
以分别心区分时,说某类法有,需要被胜义观察因找到,而说另一类法有,需要被世俗观察因找到,因为二者的对境不同。如果说其中一方的“没找到”不妨害另一方的“找到”,那么,如果说实有存在的话,就应该被无明找到;姑且说它找到了,这样一来,被它找到的实有就无法被其他因遮破。把被无明这个根本的迷乱因污染了的六识找到的诸法安立在有的范畴,而把无明这个根本的迷乱因找到的诸法安立在无的范畴,这样的做法真是奇怪。先将找不到和找到无二者区分开来,然后继续将它们计为无遮,但这仅仅是遮止了所破,不是无遮。仅仅遮止所破到底是属于找不到,还是属于找到无,值得细究一番。
说“有”,那它就必须被“能找的心”找到。依据别别不同的对境对应别别不同的心且相互不妨害的这个说法,如果说有“实有成立”的法,那就应该能被实执找到,且被它找到的也应该是实有成立的法,那么,这个实有成立的法是无法被胜义观察因遮破的。为什么?因为眼识看到的法不会被意识里想到的法妨害到,那么实执找到的法就没道理会被胜义观察因妨害。因为二者的对境不同,找到这二者的那个“能找”也不同,而且一方的找到又是另一方的找不到,所以这二者之间不可能有少许的妨害。
因为世俗因和胜义因之间的差异很大,所以认为一方的对境不会被另一方妨害的话,那么,由于实执和胜义观察因这二者间的差异更大 ,所以更可以认为一方的对境不会被另一方妨害。事实上,如果因为世俗和胜义中都没找到,就承许这个无就是周遍的,而如果因为二者中的任何一方找到了,就承许将其承许为有,这个说法其实暗设了前提,即如果六识都没找到这么一个法的话,它就是无,相反,六识找到的所有法应该被承许为有。为遮破这个认知,佛陀便说:“眼耳鼻非量,舌身意亦非。”如果龙树菩萨还住世的话,可以问问他:真诚地相信世俗谛和真诚地相信实有成立这二者之间有何区别?
(35/17分40秒)依食物而产生的贪嗔,其实是因为心将食物执为实有而产生的,除此而外,找不到贪嗔的来处。不把所谓“世俗中有”理解为于实有成立的有,反而认为诸如净、清净、名言识和世俗因也同样存在于佛陀的心相续中,这其实是在说:无始以来,被无明执为合理的都合理,不合理的都不合理。
既然你们说承许四大形成的这个身体是解脱道的所依,那当然也可以说它们是产生贪嗔痴的因;换言之,不依靠四大种形成的这个身体,就无法生起智慧;同样,不依靠它,烦恼也是无法产生的,而离开这二者的才是佛法的中观见,否则,就变成外道了。
佛陀在《楞伽经》中授记龙树菩萨“能坏有无边”,那么,将龙树菩萨开显的离开有无二边的中观见说成是“有则实有中有、无则胜义中无”的这个说法,其实是再一次把龙树中观见放在了世俗有无的范畴里面抉择,我无法确定这样做是否会毁坏龙树教法的精髓。
概括而言,对自心所建立的一切尚有少量的承许是自续派,而将所承许的一切无余遮破是应成派。若非这样,佛陀就没必要宣说“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应成自续的根本区别在于,因为自续派承认自方承许、胜义有和无实有,所以它是承许二谛双运的。而应成派则是见无实即见世俗诸法如幻,所以,菩萨十地的境界和具五决定(金刚持的异名)的报身等,虽无法被量成,但是必须承许。
因此,只要对世俗义深信不疑,那么就永远不可能对出世间义生起信心。月称论师说:“世出世间法任何时候都不相同。”“相信世俗因,修道成无义”这也正是佛陀为何说作主圣道的,并非眼耳等诸根,而是另有其主。佛陀早已明确了,无始以来,轮回里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六识之上的,即便这样,仍然要去承认它们的话,那希求空性的意义又何在?
认为中观各大因不破色等诸法的显现分,而是破它们的根因无明实执的耽著境,深究这个区分,就知道它其实等同于在承认无明的耽著境是合理的。对已经证悟空性的人而言,将色法分为所破的色法和不需要破的色法是可以的,也是能够完全能理解的。但是,对无法将色法实有和色法有区分开来的普通人而言,说要破这么多,再留这么多,就好比是留着幻象的鼻子不去破,反而去破象腿。根据于胜义观察有无是世俗而非胜义的说法,观察有无四边生也应该属于世俗而非胜义,如此一来,在世俗中会找到一种不在四边生范畴内的“如幻生”,而它在胜义中是找不到的。因为世俗观察找不到这么一个叫“如幻生”的东西,所这个“没找到”没用;虽然胜义中也找不到它,但它这个“没找到”是有用的,这种想法,是把胜义谛建立的根本仅仅当作世俗谛来相信。
破四句生被当作世俗因时,所谓“生”就无法被断定为只有四种方式,这样一来,用四句生或四边生去遮破“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说实相非有非无,远离四边戏论,和将其囊括在无自性这一个词汇中去说,对于一个已经证悟空性见的人而言,并无任何区别。但是,对于初学者而言,他们对无实有的理解和无瓶的理解是没有区别的,所以按照这种理解而言,证悟无瓶的这个心,在第二刹那时,就要在心里现起瓶子这个所破基,因此,入根本定时,也不能离开世俗的庸俗显现,如果这就是所谓的二谛双运,怎不令人恻然呢?
抛开凡夫心前显现的这个实有,需要另寻一个新的实有的话,就得在这个无明之外,另寻一个无明,因此,也需要努力在这个贪嗔之外,另寻一个贪嗔去破。
持有瓶的心不是实执而是正量的这个宗派,一定会在心里毫无违和感地建立起有一个东西叫无自性的观念;尽管如此,就像必须要区分执有瓶和执实有之间的差别一般,也必须要区分执空性有和空性如幻有的差别;对此,没有证悟空性的人,因为无法经验性地知道什么是空性,因此,对它实有成立与否,是无法区分的;而已经证悟的人,任何时候,心里现起空性时,因为都是以无遮的方式现起,所以也无法对此加以区分;这样一来,根本找不到能区分的人了。
因为没有些许的自性空,所以也没有些许的自性不空,这种说法简直让人啼笑皆非。这比起说皇上非国君和皇后身不净,更让人觉得不可理喻。因洞见其本质,所以寂天菩萨在《入菩萨行论·智慧品》中说:“否则观不净,将违世间见。”
如果只承许那些不被世俗因妨害的法,那么因为所有世间法,究其根本,都是实执,所以就需要承认有一个不被实执妨害的法。承许色声香味触等普通根识的对境存在又有什么用呢?按照你们所谓的胜义因和世俗因应互不妨害,二者的对境和想法也不相同的说法去思维时,智者“照见阳焰为阳焰”的智慧是无法妨害愚者的将阳焰执为水迷乱识。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说法不是观察唯一实相的因,而仅仅是分析别别显现的因。
月称论师宣说胜义谛时,将世俗中建立的一切摧毁,而在宣说世俗谛时,将胜义谛置于平等舍,仅随顺世俗中的大势因作他方承许。但是,如果将关于出世间的境和有境的所有论述统统摄入世俗因进行抉择的话,那么开演中观之道的意义又何在呢?
在世俗中非有和胜义中非无的中间寻觅一条中道与“陶罐不是没破但也不是没有”如出一辙——极能迎合世俗对显现的认知。
如果圣者的智慧和世俗普通人的分别心存在以互不相违的方式融合的可能性时,二谛双运才会有出现的可能性,除此而外,二谛绝无双运时。
如果唯识宗的智者们是没找到外境义,而不是找到了个无,那么,比他们更智慧的中观宗的智者们同样是没找到实有,而不是找到了个无。比如,找丢了的绣花针,先是因为什么也没找到,所以那个什么也没找到的心将绣花针执为无,但是,当后来绣花针再次找到时,那时又将绣花针执为有。因为之前执无的那个心的对境不同,所以将绣花针执为有的这个心对将绣花针执为无的心不产生妨害时,绣花针的自性就会堕入时而有时而无的情形。因为除此二边外,再无其他可能性,这样一来,确定只有四边生和四句生等,并以此遮破的做法毫无意义。
因为执实有的心和执无实有的心二者的对境更不相同,所以断无道理去说一方会妨害另一方。如果说因为势力大小会造成妨害的话,那么具贪之人执女人为净的那个心岂有不妨害阿罗汉观女人为不净的那个心的道理呢?所谓势力大小,完全是依据普通人的分别念而安立的,所以也就是通过世俗来安立。根据月称论师的宗旨,强烈贪欲引发的悦意,强烈嗔恨引发的不悦意,以及由更加强大的实执感形成的山河大地等等这些外境的建立,自佛陀以下,动物以上,只能是自方承许和他方承许二者中的任一方式来安立。虽然说灯的亮和它熄灭时的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于所知实相安立火与水、热与冷、重与轻等违品,尔后再去说世俗和胜义不相违的话,那么无论用二谛中的哪个因去观察,都绝无解脱的可能性。
对一个事情的看法,孩童时期的心和老年时期的心之间存在极大的相违性。如果明白这一切的话,那么对圣者的所量和凡夫的所想不相违的说法就会唏嘘称奇。
总之,所谓二谛,于普通人是一谛,于圣者是另一谛,因此,若将普通人的实执和圣者所照见的一切掺杂在一起的话,那么不可能对不可思议的境界产生些许的信心了。要明白,只要一直贪著于可思议的境界,那就丝毫都不曾出离世间。
所有内外宗派的宗派思想和世间普通人的观念全皆相违,所以,最上宗应成派的思想和世间普通人的观念不可能没有差别。胜义于胜义才是胜义和世俗于世俗才是世俗的说法,究其本质,跟水于水湿润,石于石坚硬的说法是一个道理。那么,按照承许坚硬和湿润无违双运的说法,就可以说石头在水中一直干而不湿,水在石头上永远湿而不干?那样一来,当然就可以说,周遍于世间的无明和周遍一切的佛的智慧就融合在一起了,因此二者也不相违。
应成因的根本之一是:眼和耳的显现不一样,鼻和舌的显现不一样,最后意识里的各种想法也会相互打架,而中观要完成的就是帮助你超越前六识的无穷分别,最终走向真胜义。如若不然,由于执持世俗所思所想的一切一方不妨害另一方的观念,因此先将名言认知安立为正量,尔后再去区分跳蚤、耗子、猫、狗和人等不同众生认知上的差别,这样的做法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六道有情和他们的显现全都是世俗谛,加之,事实上,一方的显现一定会被另一方所妨害,因此,究竟来看,没有一个所谓的世俗谛。如果人的显现不妨害饿鬼的显现,饿鬼的显现不妨害天人的显现,那么佛的显现也就没有机会妨害众生的显现了,因此,不净的一切都会永远原封不动地留在原地。
无自性的词句无法遮破无自性的事物,这种说法实际上是背离了自方承许。《回诤论》中的“遮破无自性,即成有自性”,恰恰是应成见,而不是自续派的承许。同理,若有少许不空,应有少许空;若有等等少许所破,应有少许能破故空和少许能破彼之因;这些都是应成派的说法。依此因类推,若有实有的所破,应有实有的能破;若有如幻的所破,也应有如幻的能破;若绝无所破,也应成根本不需要能破。这便是中观宗所建立的宗派理论。
要摧毁他方或世俗见,就必须将有无二边都摧毁。佛陀如是授记开显中观教法的龙树菩萨:“其名号曰龙,能坏有无边。”承许二谛双运能承当“于金无土的无,于土有土的有”,实际上,是在承许世俗普通人的分别念和佛陀的智慧是无违双运的,如此一来,承许无明和胜义观察因也是无违双运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知明便知暗,知善便知恶,因此也可以建立明暗双运和善恶双运,那么,一切相违的法都是可以被双运的。
实有、事物等这些话,仅仅是世俗普通人为了实现相互沟通,达成的词句上的共识而已;但如若因此,你自以为明白了其义,并宣称胜义中无而有,那么遑论明白佛陀为众生宣说的不可思议的法,就连一个对应成见解稍有领悟的人看来,于你而言,要按照应成自宗的方式对空性生起定解,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把世俗中建立的一切安立为如理的这个说法,无视不会说话的猫鼠和比它们稍强点儿的小孩和愚者们的显现,认为名言量既不像极具智慧的应成派那般聪敏,也不像世俗那般愚钝,而是一种处于二者中间的世俗老者的认知。
以自性空入定时,无一法可破,后得位时才需要去破;但按照你们承许二谛双运的说法来看,这个说法很难成立:虽然先证悟了无实有,不过此时,心里还是会生起无实有本身依旧是实有的想法,如此一来,证悟空性又有什么用呢?
区分好的分别和坏的分别好比是执美为美是好的分别,执美为不美是坏的分别,执实有为实有应是好的分别,执实有为如幻应是坏的分别(《中观精要·讲记》音频39/22分20秒:慈师说他没明白这两句所表达的意思,感觉另有所指。),如果不去这样区分的话,显然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总之,这个承许二谛不相违的说法,实际上,是在承许众生的分别和佛陀的智慧所不相违。
宗喀巴大师的究竟意趣没有重视应成自宗没有承许的这个名言说法,而是将自续承许和自主承许说成是一个意思,而且说自他两种承许的终极指向不是补特伽罗,而是事物的实相,因此把承许事物以自相的方式成立安立为自续,而承许事物不以自相的方式成立则被安立为应成。
感觉这种说法是把自方承许和他方承许看成了世俗普通人的争吵,把争吵双方达成的共识当成了建立一切的根本。所谓出世间法,顾名思义,就是一种超越世俗言思的法,因此,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时,方能趣入圣者之境,也正因如此,除非承许圣者的智慧和众生的分别念之间有着高低之分,不然自方承许和他方承许也无从说起。
说实话,跟愚笨的人说的话要切合他们愚笨的思维方式,否则无法沟通。但是,若因此把沟通的这个媒介本身当成一切所知的根本,则令人倍感唏嘘。
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月称论师在《显句论·观我品》中说:“如对蔑戾车,余言不能攝,世间未通达,不能摄世间。”这首偈子是说对边鄙之人要用边鄙之语沟通才能晓之以理。同理,尽管佛陀已出了世间,但要同世间人宣说圣法时,就得按照世间建立的说法宣说,除此而外,别无他法。
“比量不得真实义”中说的这个所谓的比量,便是如今在藏地盛行的三相论式。使用这个论式时,因为所涉及的一切都要是自续或自宗承许,所以因法事三相也都要是自宗承许。这时,因为所谓他方承许因和应成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差异,所以仅仅是以他方承许的说法遮破他方建立的合理性,因此,所说没有共同的显现和自续的论式无法成立之间并无差别,这样一来,对自宗没有自续承许的月称论师的应成见构不成任何妨害。月称论师说:“立论和驳论双方所谓的瓶子无法共同成立;同样,法和因也无法共同成立,因此,仅应成就足以遮破对方的承许。”
如果自续承认他方的有,那么就得于自方承认无;反之,如果承认无,就得于自方承认有,这样就等于承许了二边,因此,如果是究竟的中观宗,就不应该是自续派了。
于自方承许世俗法叫做自续派,与他方承许则叫应成派,因此,应成派没有任何与世间共称的法,这就是没有共同显现的的意思。一切错误的根本是把如幻的显现当成了世俗谛,这样一来,于应成派现起的任何显现也需要在普通人那里现起,因此,自然也就不能去说没有共同的显现,但是,由于所有显现和分别都感觉是真实和实执的缘故,所以共同的显现其实是不可能有的。所破是由能破之理来抉择的,而不是由其他一个心识来抉择的。执根本没有柱子的断见,或从中观定出定时,可以被眼睛看到的,被手摸到的,且具有托举房梁作用的柱子等被所知障污染的所有显现,会依旧在那里;虽然,这时自心不相信这些显现是真的,但是暂时还需要于他方承许,这就是应成派的世俗谛。
对轮回的根本无明所造成的实执这个所破不加以胜义的简别,而只是在它前面用一个“唯“字修饰限制的话,那我们流转于轮回就显得毫无道理了。离开无明实执,若要安立一个新的所破,除了遍计所破外,还能有其他什么呢?
世人分别心的执著方式是:有色法,有实有的色法,有实有成立的色法,有自性有的色法,仅此而已;心不去遮破于实执产生的显现,而去另寻一个所破,这种做法说明你们对无明和无明导致的二元性的迷乱显现深信不疑。
对所谓有法进行观察的因仅仅是对世俗显现法进行观察而已,比如,这个的颜色是黄色吗?这是黄金吗?这是块好的黄金吗?它来自哪里?离开我的所见,它自己还能是黄金吗?它是真的吗?它实有吗?这些之间的差别,仅仅是由于凡夫认知能力的高低导致的,但究其本质,不难得出,这些无一例外地都是世俗普通人的分别念而已。
“如何是瓶”的观察因若找不到瓶子的话,那么,在这世上,就无法找到那个能找到“瓶就是瓶”的心了。说一个东西就是它本身,需要依据,不然,没有哪个理察师会承许这种说法。总之,所谓找这个“法为何是那个法本身”就是要找到它为何是它自己的那个原因,根本找不到那个原因,但却依然固执己见的话,那么要中观见又有何用呢?
是或非,都得有各自相应的理由。先断定找不到是非二者的理由,尔后却把于是非建立的一切承许为合理,这种做法完全毁坏了中观见,而且还会导致要去承许一种在“已去无有去,未去亦无去,离已去未去,去时亦无去”的范畴之外的第四种“去”,即“非去”。承许这个“非去的去”会将龙树父子的所有中观之理毁坏殆尽。
认知能力一般的人也知道“是”能破“非”的道理。因为我们的显现和所见都不及佛陀的无量分之一,所以愚者和佛陀之间就圣法相互沟通时,佛陀只能是采取应成派的他方承许,不可能作自方承许。
简言之,提出所谓的二谛无违双运之道,感觉是有意想把佛陀的遍知和众生的所知无违地捏在一起。如果真这么相信,那别说相信有轮涅这回事,就连轮涅这个词汇都不可能相信。
承许没有共同显现的宗派,它自宗不会去以量建立一个独立于“有法”之外的“如幻的有法”这样的概念,而他宗所建立的正量其实又起不到正量的作用,因此,以正量建立的立宗和因法等是不合理的。
后译派学者们安立所谓没有共同的显现时,通过把有法独立出来的方式,假立了一个新的“没有共同的显现”,因为这样,他们便可以建立起有共许的立宗和因法等,但是,这样的做法会导致,于胜义谛仍说世俗谛有,也就是说圣者的显现和普通人的显现是一样的,如此一来,因为一切皆成共许,所以就不用再去区分因法事三相有无共许的差别了。
从修持中观见的中观师在后得位时的见闻觉知而言,他们与世俗普通人和精于宗派遍计的世间学者们的之间当然是有共许的有法、看法和想法。但是,成佛的圣道有别于世俗普通人的显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月称论师才说:“首先就得遮破这个所谓共同的显现。”
无瓶的无遮和万法以及于万法无的无遮二者完全不一样。同样,雪域前派认为的诸如“虽无瓶,但还有个能容纳瓶的地方”的非遮的说法也有其回避不了的缺陷。总之,将有无都执为无的心,只能是于分别心或世俗的所缘境分别有无,所以才说因为心前没有了任何对相的分别,那时的心才一定是解脱和寂静的,对此,寂天菩萨在《入菩萨行论·智慧品》中说:“若实无实法,悉不住心前,彼时无余相,无缘最寂灭。”此时所说的心,就像寂天菩萨刚才所诠的那样,是世俗心,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月称论师也在其《入中论自释·第六现前地品》中说:“痴障性故名世俗,假法由彼现为实,能仁说名世俗谛......”第二世手持白莲观音上师·根顿嘉措深谙此义,所以也在他的《了不了义难义释》的结尾处说:“无遮并非指兔角无,而恰恰指的是你们所承许的离戏的说法。”
因此,如果对这些大师们的所说的话不加修改而如实去理解的话,就应该知道所谓世俗心和于世俗心实有就是所谓世俗谛的意思。如果于自续承许正量的话,那么他方的想法也必然要被自宗所承许。所谓应成,仅仅是为了指出对方的相违之处,佛陀在说宣说空性时的做法也是如此,应成派的他方承许也是这个道理。尽管应成也说自方承许,但此时的“自方承许”仅仅是为了方便与世俗进行逻辑推理而安立的名相而已;虽然应成派以没有承许的见解无余遮破他方,但是鉴于他方的所知障,不得以于名言去说自宗承许,但是,这和你们所谓的自宗承许完全是两码事。
中观应成派因会遭受一些来自世间学者们的戏虐,因此,佛陀才说:“世间与我争,我不与世间争。”世间的这个争法,不是通过因法事三相,以建立有共同显现的方式,与佛陀展开的争论,而是在不违背世间所有的看法、显现的方式和想法的前提下,企图以无勤的方式去证实已知的,所知的和未知的一切。如果这些显现都是无患正量的对境,那么没必要为了找到另一条路而努力地闻思修了。
总而言之,所谓正量,就好比是老鼠把什么东西都看成所偷,猫把所有老鼠看成所杀,以及人把这二者都看成不合理。眼识没找到声音,而不是找到了没有声音;按照这个说法,可以把胜义观察的心比作眼识,把世俗观察的心比作耳识,这二者一方找不到另一方的对境,但二者的对境于各自具境的心前有;感觉这个说法似乎在帮衬建立二谛无违双运的合理性;但是,胜义观察的方式就像是眼识去找声音一般,一旦它找的方式从一开始就错了的话,那它找到的无可能就没用了;但是,它找的方式若没有错的话,那么因为它没找到,所以找到的为什么不是“无”呢?这样一来,胜义观察也就成了名言所知,对此,宗喀巴大师自己也是承认的,所以,因为世俗观察没找到,所以一个无法承当“无的有”却被胜义观察找到了的话,实属稀奇。
对于不相信离四边戏论的宗派而言,没有承许即是承许。虽然他们对于“胜义无”作出了“有等”的观察,但是,对离戏这一佛法核心具有信心的人们而言,对世间庸俗之理,无论有利还是有害,一定会不喜不悲,不迎不拒。
相信庸俗之理时,会认为看见佛陀的双足却不见顶髻和刚刚诞生的报身永远不灭等的说法极为不合理。总之,世人的想法丝毫无法企及般若彼岸,所以,如果完全相信三相推理等大学者们所推崇的逻辑分别公式,那么,不用说能证悟究竟的空性义,就连于自相续成熟世俗菩提心也会是一件飘渺无期的事。事实上,他们把对世俗显现和所有名言分别彻底的绝望误认为是空性见。
因为离开有无二边的中观见超越了世间庸俗之理,所以任何以有无建立起来的世间学说无法将其遮破。《入中论》说:“二元论不合理,因此,依靠有无所作出的遮破和回辩,无论以什么方式,都无法与中观见分庭抗礼。”
如果取信于这类的世间学说,不用说证悟实相,就连佛经中记载的那些超出了世间认知范畴的典故,也都难以相信。比如,佛身放光,《阿难夜里点灯经》的历史(慈师说他不清楚这部经到底指的是什么。查询后的大致结果有三:一、阿难问佛为何阿那律是天眼第一的典故;二、阿难问佛陀何种善根使佛陀获得无量明灯供养的果报;三、还有阿难问佛是什么原因贫女难陀被授记为灯光佛的典故。),杀了九百九十九人后成为释迦佛主要弟子的央掘魔罗的故事。央掘魔罗追杀佛陀未果,便于佛前放下血迹斑斑的屠刀,立地而坐,以金刚智摧伏二十种萨迦耶见,现证圣道。
这些做法,总的来说,是企图以庸俗的想法妨害圣者之理,因此,凡是希求解脱者,必定要对此弃之断之。
一碗水,因为六道众生所见的不同,都知道要将其分开六种去说,但是,却将佛陀和众生二者所见的瓶子说成是一样的,这个说法极为荒诞。
对没有共同显现的的究竟理解方式是:因为没有证悟空性,所以不以实有的方式去缘取色法时,就无法缘取色法,因此,缘取色法时,就只能是以实有成立的方式去缘取。“色法为有法,应成非实有,缘起之故。”尽管以此论式能成立色法非实有,但是有法本身没有成立,所以在没有缘取色法时,就不会有能承当理证的基法,此时,他方所作的承许恰恰就是应成派发出太过的所破基。
具有智慧的圣者和世间的疯子对话时,疯子说的有不是圣者自方承许的有,而是圣者以应成的方式跟疯子讲:“如果你的那个是的话,那当你说是的时候,其他的就变成不是了。”因此,这个没有共同显现的因,仅仅是以名言的方式,去完成双方之间的交流,而且,世俗之理也仅仅是以名言的方式安立的;同理,疯子的道理也是疯子他自己安立的,所以于他而言,说这些道理都是真的,倒也说得过去,但要知道:疯子所见的金子,在我们看来,又可能是石头;我们凡夫的有,也有可能是圣者的无。各自心前显现不同相的凡夫之间没有一个共同显现的所知,而那些已经见道的圣者,是为了顾及世间显现的情面,不得以而去随顺世间庸俗的说法。当外境或所知障的力量变弱时,从外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识对外境的恐惧会变小,最后,与能知本身一味的所知融合后便获得双运之身。
如果说于三大阿僧祇劫积累资粮的佛陀仍旧和凡夫有一个共通的显现,那为何还要求佛果呢?倒不如求金银珠宝来得更实际。
清净烦恼障说到底是为了清净所知障(慈师说现在有人说这是根大师自己的观点:打心里认为有桌子是烦恼障;打心里认为没有,但眼睛可见的桌子是所知障。实执是烦恼障,仅二元显现是所知障。这本书里的个别说法不完全是前译宁玛自宗的说法。)。遮蔽究竟实相的二障中,先断除的是具境心的烦恼障,而所知境的障碍或所知障,诚如达仓大译师所言,在断除细微身障(慈师说这里的身障应该是指细微的实执感)之前,是无法断尽的。(慈师说他不知道达仓译师的著作里是否有说过这样的话)
总而言之,中观宗不能有自方承许的说法,事实上,这等于是在说中观宗不能如实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深深思维遍计实执和宗派增益出来的我执和实执等时,就能体会到凡夫位的我的那种世界观被它们改变了,因此,我想所有这些的遍计实执会不会是将人引向解脱道的阶梯呢?
宗喀巴大师曾说:“因为背离了佛法,尽管长期勤修,却只见毛病渐长,我执更盛。”宗喀巴大师说耽著我执的对境性的那个我便是我慢。按照这个说法,将自己观想成金刚萨埵的我慢和认为万法的清净自性是我的我慢,如果没有离开宗大师所说的那种我慢,那么作这些观修也只会使我执更盛。所以,开始将一个完全与“庸俗的我”不同的“我”执为我时,就意味着开始推门希求见到佛的本来面目了。
“这个是那个,如果是这个就应该是那个,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这就是三相推理。这样的推理拿去说给山中的猎人们听还行,但是将其视为世俗观察的正量的话,实在是令人错愕不已。
如果认为凡夫的正量可靠,那么执事物实有和女人身净等也应该被视为正量,但事实上,世俗心里势力大的习气所导致的这些显现没有被视为正量,而是把建立在它们之上的逻辑推理当成了正量,这种做法的意义何在?སཾ་བྲཾ་ཏི (英音:Samvrti / 汉音:桑巴RA谛)这个梵语词汇,被以前的译师翻译成了世俗谛,但它其实是迷乱的意思,即对清净真相的障蔽或对一切的迷惑不解,因此,所谓世俗谛,应该理解成“迷乱的真实”。
如果七相木马因无法遮破木马的自相成立,那么串习五道也就无法断除烦恼和所知二障。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即需要以理作出诸如”胜义的贪痴是所断,而贪痴本身不是所断”等很细微的界定和区分。
把心看见的世俗显现和没看见的本来无生这两个方面所建立的所有理论混杂在一起,实际上说明,连所谓世俗谛这个词汇的定义都还没弄明白。月称论师也在其《入中论自释·第六现前地品》中说:“痴障性故名世俗,假法由彼现为实,能仁说名世俗谛,所有假法唯世俗。”“愚痴障蔽自性的缘故”、“由彼造作的假法”和“能仁佛说假法乃世俗谛”是佛陀关于什么是世俗谛最清晰和确凿的教证。其实,我们要明白,世人公认的现量和比量只是介于两个不明白的心之间的细微的心识活动而已。
因为胜义无,所以无法承当无,而因为世俗有,所以可以承当有,按照这个逻辑,就会产生下面这种颠倒认知的说法:因为圣者的胜义观察前有,所以无法承当有,而因为世间迷乱显现前无,所以无法承当无。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引出更加荒诞的说法:尽管幻马为马,但是因为智者没找到,所以无法承当无,而因为愚者找到了,所以就能承当有。
虽然用世俗谛和尽所有这样的名言词去说“心能找的法”,但是,由于这里所谓的尽所有,指的是心力极其孱弱的凡夫的分别念能找的所有法,所以如果笼统地分析一下凡夫分别念能找到的这个尽所有,就知道它应该含摄在自轮回的顶端到最底层的地狱之间的六道有情和东山之巅到西山之间的虚空里面,这样一来,佛的尽所有智就等同于凡夫分别念能找的所有法。
但这个尽所有好比是你在自家的灶台底下发现的金子;你一直不知道自己找到的这个东西是什么,直到别人告诉你这是金子时,你才知道原来这就是金子。就像这个比喻,我们找到的所有世俗法本身就是离戏的法性,我们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因此,我们应该对宁玛派的本来解脱的普贤王如来的大圆满教法生起些许的信心。
观待理是自续派的比量,作用理是能承当的应成派之理,(慈师说前面这两个理,根大师的说法和前译派不太一样。)证成理是通过因和法有共同显现的方式去寻找的,法尔理只能依靠非世俗逻辑推理的胜义理而获得。
所谓万法指的是心前能现起的所有法,而“见万法无”指的是于心前不见一法,如果说这是一种歪曲,那么被歪曲的所知境和具境心二者也是见不着的,这样一来,与其通过百千万劫积累资粮证得无境无住的甚深圣法,倒不如就以这样的方式证得——不用担心会沦为断见。
心和境逐步得到转化后才最终得以成佛。不过,我们执著世俗中的山河大地、女人和酒肉等显现是一个无始以来人尽皆知的事情,因此无须在它上面再去平添什么能立因。
男人不会觉得母老虎美,所以也不会对它生起贪欲。公老虎也不会觉得女人美,所以也不会对她生起贪欲。究其根本,这是因为在老虎那里成立的三相推理,在我们人类这里就不成立,反之亦然。从动物和人类之间没有共同的三相推理,可以推出在色究竟天之下和地狱之上的所有六道有情之间也没有共同的三相推理。
无始以来,六道有情习惯于着相:水,对于地狱众生是烈火;对于天人是甘露;对于人道是水;对于饿鬼是脓血。换一次身体,所见的相也会跟着变。这些不需要费力去解释,众生知道各自心前显现的是水还是脓血。因此,努力去找一个无始以来就未曾出现过的,但与我们的心如影随形的无明的对境——所破的实有,实属稀奇。
如果说无瓶、无柱等与世间共称的显现相违的缘故,便是断见,那么所谓六道众生没有共同显现的实有岂不成了所有断见的老祖?
世俗心最大的习气是实执,因此,圣天论师说:“若住于庸俗,即被烦恼侵。”认识了心,但还要攀缘外境,这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没必要再去找一个无始以来就有的我执的一个新的对境。
承认自性的数论派将自性执为实有;不承认轮回的顺世派将无本身执为实有;有些宗派说兔角虽无,但它却不是于空基有法无的空性。按照他们的说法来看,先把万法分开放一边,再把它们的无分开放另一边,这样的做法只能是在成立谛实空,这样一来,直到真正成佛为止,是无法证悟空性的。你们所谓的不知道如何在没有空基有法之上安立空性的说法,可以理解成没有瓶子这个空基,所以不知道如何在它上面安立瓶子里面的水。
如果你们依靠因去成立不实有时,必须要有个空基有法的话,那么请把实有当作空基,把那个无当作空性;同理,请把所谓自性无的自性当作空基,把它所谓的无当作空性。认为实有和自性空是理所破而不是所破基的想法,是以为瓶子上面有的这个实有的污点可以被各种见解的水清洗干净,但这就像美女洗澡一般,洗得越多越勤,只会把实有的面目洗得更加地清晰可见。
因为不实有的兔角没有空基,所以不在空性的范畴之内,而因为不实有的瓶子有空基,所以它在空性的范畴之内。这样一来,就等于在说:所谓没角尖的兔角,因为它没有空基,所以不在无遮的范畴之内,而没角尖的牦牛角的空基、所破的角尖和那个被它空掉的空分都是无遮。这实际上是在暗设凡是无,就需要对其安立一个能依的有,而某个有法要变成无时,也需要给它安立一个无才行。圣天论师说:“若前有后无,故彼成断见。”
实执,无始以来就有,而实有,无始以来就没有,为何要将这两个混杂在一起呢?把进入大乘和大乘宗派的差异看成是同一个东西,把有部宗和大乘菩萨的发心说成是同一个东西,这样的承许方式着实令人惊讶。他们心想只要心里有合乎大乘标准的发心就算是入了大乘,而自己是四个宗派里的哪一宗派,其实没什么区别,这说明他们其实是不会承认十地、五智和三身等说法的;要知道,仅凭为利众生愿成佛的这个想法是不会成为菩萨的。
尽管数论派也认为他们是为了自他二利而去寻找一个他们认为究竟的果位,但是由于基道果的见解错了,所以他们所说的那条路是一条不圆满的路。由于有部宗所说的菩萨真诚地相信究竟三乘,阿罗汉的果位、色法和心法的相续和断灭等有部宗所有不共的见解,所以他们所求的佛果,在大乘看来,不是真正的佛果。因此,他们为了获得那种果位的心也不会成为大乘的发心。有部宗的行人们想证得佛果是建立在有部宗自己所建立的基道果的见解之上的。在有部宗看来,上上宗建立的那些见解基本上都是错的。一开始就走错路的人,希求究竟果位的期许最终只能落空。
将花绳误认为是蛇而产生恐惧时,尽管有人说那不是蛇,但是有些胆小的人,事后每每见着花绳,仍旧心有恐惧感,这说明那种恐惧的根源其实还没有消除。鉴于此,寂天论师在《入菩萨行论·智慧品》说:“如彼幻术师,亦贪所变女。”就像幻术师,明明知道自己变出来的女人不是真的,但还是会生贪爱之心。同样,尽管他也知道自己变出来的老虎不是真的,但也会生起恐惧之心。那么,遣除胆小者执绳为蛇的恐惧,最好的办法是请一位胆子大的人把那条花绳扔掉。因为,这样一来,被误认为蛇的花绳这个基法和在它之上生起的蛇的幻相二者都会一并消失得无影无踪。否则,就算再怎么跟他说这不是蛇,但当他再次看见花绳时,毫无疑问,那种恐惧感会不由自主地生起。
虽然彩虹和影像看起来很真实,仿佛可以用手去触摸,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对这个无质碍性的识的理解,如果它跟龙树菩萨在其论典中所宣说的如幻的见解不相吻合,那么无论是应成还是自续,都无法于有实宗成立如幻义。比如此论式:柱子为有法,如幻,缘起故,比如彩虹。对于此时他方所举出的彩虹的同品喻,中观宗认为,因为他方心前这个如幻彩虹的现起方式与幻身的现起方式完全不同,所以没必要在此安立这个彩虹的同品喻。
随着年龄的增长,因为儿时的童趣没了,所以我们不再喜欢儿时玩的过家家,为了生起它,我们在一座中努力修持它;因为壮年时享受五妙欲的能力没了,所以我们不再喜欢女人了,为了生起它,我们在同一座中努力修持它;因为老年时的贪欲没了,所以我们不再喜欢房子、车子和票子了,为了生起它,我们在同一座中努力修持它。有人说这就是阿底峡尊者提出的将一生需要修持的整个佛法于一座中来修持的关要之所在。(下面的儿时比作别解脱戒的修持,壮年比作菩萨戒的修持,老年比作密乘戒的修持,整个教法比作我们一辈子要修的法。)如果把这个作为同品喻来类比性地对五道十地次第的修行方式进行区分,即是:进入加行道后,反而要去努力修资粮道;进入八地后,反而要去努力修初地;获得佛果后,反而要去努力修资粮道。概言之,即便是成佛后,似乎仍需要在密严刹土的莲花垫上圆满修持从声闻乘到菩萨乘再到密乘的整个教法。
(根大师用上面这个类比指出格鲁派所理解的阿底峡尊者提出的将一生需要修持的整个佛法于一座中来修持是不合理的。但是我问了格鲁派的几位格西,他们说这要看你怎么理解阿底峡尊者所说的“一座”中的那个“座”,它的藏语是“垫”。因为藏语里的“座垫”和“人身”都发“垫”这个音。根大师这里用的“垫”是座垫的“垫”,而格鲁派说那个“垫”是既要理解成“座垫”,也要理解成“人身”。所以,格鲁派对阿底峡尊者这个修持关要的理解是我们要用一生去修持整个佛法,而每一座应该有各自主修的法。《中观精要·讲记》音频47条/3分30秒,慈师在讲记中对根大师的说法作了他不共的阐释:慈师说按字面意思理解的话会感觉这里再说整个佛法的修持要从上至下倒着来开展,但根大师所表达的应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这样去理解:能在一座中去修持和现证加行道是因为有了资粮道的断贪等诸所断的修持;要实现八地的修持也是需要一地到七地各阶位的修持作为前行基础;要证得佛果,就需要从资粮道开始,通过三十七道品的修持,不断地集资净障,从而彻底断除二障,获得无上无修圆满的佛果。)
颂曰:
超越有无二边之智慧
龙树父子宗旨之精要
雪域新旧各派诸先贤
所有见解汇于此善说
从我上师大悲之心间
慧日光芒普照十方界
虽然无明邪见蒙蔽我
慧心之花绽放笑颜开
十方三世诸佛心甘露
教理窍诀如炼截磨金
不可思议纯净之法界
累世宿缘故我心能持
然而文殊怙主所宣说
一切教法汇聚善说海
无奈遭受无明之垢染
愿以至诚之心作忏悔
于此努力善说之光芒
即刻照耀念根心莲开
自然本智蜜汁之甘甜
息灭诸相于本体成熟
生生世世上师摄受我
甚深法性离戏之法界
愿我无误如理能证悟
通达究竟清净之法道
善道诸多方便如清风
涤荡轮回幻城秋日云
愿于无边法界虚空处
三身一味佛光恒普照
根敦群陪大师生于西藏安多的一户世代修习前译宁玛派密法的人家。他不仅通达内外二道和新旧各派的教理,而且通过实证获得成就。事实上,他真正的名号是玛哈班智达·根敦群培。我有幸于他座下听闻殊胜中观教法,后将闻法笔记呈于上师阅览。上师十分欢喜,便写下一篇愿文,并将其与一幅圣者龙树菩萨的唐卡一道赐予我。上师圆寂之际,嘱咐我务必将此笔记整理成出来。对此,我谨记于心。敦珠法王也同样敦促此事,并为此提供了誊写复印的纸张。为了不辜负他们的嘱托,弟子夏娘绒巴·达瓦桑波,于藏历第十六饶迥铁兔年十二月初十五吉日完成此事。以此善根,祈愿自他显现有别的所有众生能于无别遍主金刚持的心间获得解脱。
སྭསྟི桑谛(吉祥如意)
邪见弥漫深深黑夜中
了义甘露皎洁之月光
稀奇龙树月称再来者
今现无垢佛法虚空中
无垢法眼能辨之智慧
无误抉择法性金刚语
以此少许无二之善说
愿续前译宗派之慧命
欲将此说比作法舍利
依此所修福报愿有情
速能离开轮涅之幻城
祈愿现证中观真实义